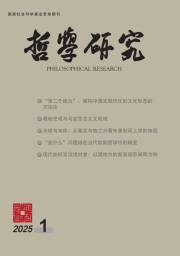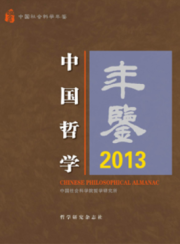首页
首页-
本所概况
哲学所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 党建工作
- 研究学人
- 科研工作
- 学术期刊
- 人才培养
博士后更多+
- 图书档案
图书馆简介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 - 哲学系
本所概况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聂锦芳来我所做学术报告

为深化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解,2017年6月21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室组织召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学术报告在哲学所931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聂锦芳做了题为《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定稿工作?——1867-1883年间的思想图景及其身后效应》的学术报告。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中国社科网等三十余位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报告。
报告内容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写作与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讲起,非常值得深思的是,在初稿大致写出的情况下,马克思最终却没有完成其整理和定稿工作。这只能到从1867年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到他1883年去世长达十六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寻求答案。这一阶段马克思的工作和思想发展呈现出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有五条线索交错进行:一是对《资本论》第1卷的修订、第2-3卷的整理和新的文献的补充、发掘,以及鉴于19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变化而不时陷入停顿;二是对西方工人运动的参与和反省,包括马克思与德国工人党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的展开;三是在资本主义“史前史”的求解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视界和框架的突破;四是在对俄国社会的研究中遭遇“跨越”与“不可跨越”的难题;五是马克思对自己学说未来命运的忧虑,面对当时业已显露出来的种种迹象和可能,马克思多次发出“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振聋发聩的慨叹。
上述驳杂的思想图景透露了身患多种疾病、并且被视为“处于慢性死亡状态”的马克思展宽的视野、清醒的自我反省和更为深入的考量,成为连接他之前的理论与20世纪西方思想史(包括哲学史)、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中间桥梁。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对这一阶段文献的整体把握和具体文本细节的解读,造成了对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乃至误读。回到马克思的原始著述中探寻《资本论》没有定稿的原因,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丰复性,也有助于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探索它的当代发展。
马克思生前没有成型的《资本论》第2卷、第3卷,以及他的晚年笔记(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一方面凸显了马克思是诚实的面对史料与原来理论的冲突;一方面也把他在论证过程中的痛苦、困惑真实的展现出来,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十几年的艰辛探索,而且体现出马克思在丰富的现实面前,对理论的严谨态度和对社会发展与人的终极关怀情怀。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至今,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不断验证了这一点。而2017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与150年前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趋势、新特征,这需要我们用马克思的方法对其进行批判分析。此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报告把目光聚焦在《资本论》出版后至马克思去世前的十六年,即1867-1883年间的马克思思想图景及其身后效应的研讨,既是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印证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发展的现实与《资本论》分析论断的契合;也是为推动《资本论》研究的深化,展示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特点,即注重对《资本论》当代性的讨论,用马克思的方法面对资本主义的新情况。
当前,国内外学界对《资本论》的解读主要有哲学的、政治的和政治经济学的三种方式。而在聂锦芳教授的报告中与会人员领略了一种文本学的解读方式,即回到马克思的原始著述中探寻《资本论》的思想图景及其身后效应,这将有助于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探索它的当代发展。在两个小时的讲述交流中,观点纷呈。学术报告圆满结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室李俊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 电话:(010)85195506
电话:(010)85195506
![]() 传真:(010)65137826
传真:(010)65137826
![]()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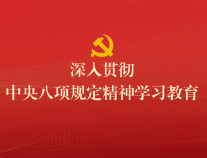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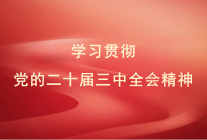




 潘梓年
潘梓年 金岳霖
金岳霖 贺麟
贺麟 杜任之
杜任之 容肇祖
容肇祖 沈有鼎
沈有鼎 巫白慧
巫白慧 杨一之
杨一之 徐崇温
徐崇温 陈筠泉
陈筠泉 姚介厚
姚介厚 李景源
李景源 赵汀阳
赵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