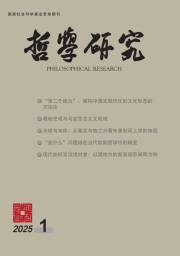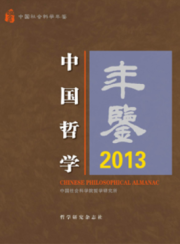首页
首页-
本所概况
哲学所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 党建工作
- 研究学人
- 科研工作
- 学术期刊
- 人才培养
博士后更多+
- 图书档案
图书馆简介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 - 哲学系
【丁三东】马克思哲学与德国理念论
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有着怎样的关系, 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为该研究奠定了基调:马克思哲学“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 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 (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成果丰富了哲学”。特别是马克思通过吸收黑格尔辩证法, 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 从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研究者们沿着列宁指引的方向, 深入探讨了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等因素在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马克思如何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如何在社会历史领域对它加以创造性的运用, 相关探讨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 随着研究的推进, 研究者们的视野逐渐扩展到了黑格尔之前的德国古典哲学, 更细致地考察了康德、费希特等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所发挥的影响。例如俞吾金、徐长福、王南湜、张盾等人分别从理论哲学、实践哲学等角度深入讨论了马克思哲学中的康德哲学的因素。[2]沈真、梁志学、崔文奎、洛克莫尔 (Tom Rockmore) 等人深入讨论了马克思哲学中的费希特因素。[3]
上述研究主要着眼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具体哲学家之间的思想关系, 并未特别关注马克思哲学与作为整体的德国古典哲学之间关系的宏观考察。当然,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还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界, 很多学者都指出了德国古典哲学内部各个哲学家思想的内在差异。[4]然而, 在笔者看来, 这些研究中把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往往整体上冠以“德国理念论 (Deutsche Idealismus) ”之名。[5]这意味着, 马克思哲学与作为整体的德国古典哲学之间关系的考察就是必要而可能的。本文就是此种考察的尝试, 而这一考察能否现实地展开, 取决于我们如何整体性地理解德国理念论。
笔者赞同, 在德国理念论内部存在着巨大的思想差异和不同的思路。但这种哲学思想立足于其开启者康德的哲学, 因此有必要对德国理念论的根本问题在康德那里的本真含义作出一个简明的分析, 把它的核心解释为“理念如何现实化”这一问题, 并在此问题的脉络中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决定性贡献。
一如何翻译“Deutsche Idealismus”?
在汉语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语境中, “Deutsche Idealismus”通常被译为“德国唯心主义”。这一翻译背后的理解和解释框架就是人们熟悉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在汉语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语境中, 随着近几年来学者们对康德、黑格尔等人哲学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把“Deutsche Idealismus”翻译为“德国观念论”。上述术语翻译的差异是汉语学界对Deutsche Idealismus的不同进路研究的自然结果, 也反映了马克思哲学与Deutsche Idealismus之间的微妙关系。
“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一概念框架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得到了最有影响力的刻画。在该书的第二部分[6], 恩格斯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它包含着两个向度。在存在论的向度上, 恩格斯把该问题表述为: (1) “何者是本原性的 (das Ursprüngliche) ”?根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他区分出了两类哲学:凡是认为思维是本原的, 乃是唯心主义 (Idealismus) ;凡是认为存在是本原的, 则属于唯物主义 (Materialismus) 。在认识论的向度上, 他把该问题作了多种表述: (2) “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 (die Welt selbst) 的关系是怎样的”? (3) “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 (die wirkliche Welt) ”? (4) “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形成一种对现实的正确反映 (ein richtiges Spiegelbild der der Wirklichkeit) ?根据上述标准,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就是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
如何看待恩格斯这里提出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解释框架, 这是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一些论者认为它过于简单, 且与马克思的思想多有抵牾之处。[7]当然, 也有些论者认为,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并不存在对立, 它们最多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因而是“一致与互补”的关系。[8]笔者在此无意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同异这个大问题。笔者仅仅想通过对“Deutsche Idealismus”的开端处康德思想的考察来揭示, 当我们用“唯心主义”这个译名来指称康德哲学时, 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这种复杂性就在于, 第一, 它面临康德文本解释的一个麻烦。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 康德专门增添了一节“驳唯心论” (Widerlegung des Idealismus) 的内容。在其中, 康德对笛卡尔和贝克莱所代表的唯心论主张进行了有力驳斥。康德在此力图证明的是:“对我自己的存有的单纯的、但经验性地被规定了的意识证明在我之外的空间中诸对象的存有。” (B275) [9]康德的证明思路是, 外部对象的存有是自我意识得以形成的基础;用恩格斯式的表达说就是, 存在是思想的根据。就此而言, 康德似乎很难被简单地归为传统的唯心主义阵营。
第二, 如何理解恩格斯所使用的一系列术语。从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 存在着从“事物本身 (das Ding an sich) ”到“对象 (der Gegenstand/das Objekt) ”的转变。在古典哲学那里, 事物被构想为自身整体性地显现的东西, 思想要把握它, 只需接受、静观。但在现代哲学中, 事物则被视为被经验到的对象;关于事物的讨论被转化成为关于事物的经验的讨论。而这经验对象 (das Ob-jekt) 乃是主体 (das Sub-jekt) 以自身为根据建构起来的。在哲学的这一现代转型中, 康德正是关键性的人物。他通过对直观和概念的区分, 否定了人的认识能够像上帝之眼一样直接地把握事物自身, 转而强调人的认识在根本上的曲行性 (推断性、间接性) 特征。因此, 他对“事物本身” (或译为“物自体”) 的讨论仅仅是在先验反思的意义上进行的。[10]相应地, 思想与对象的关系就不是“反映”, 而是“规定”———不是主体依照对象, 而是对象依照主体———这就是康德“哥白尼式革命”“人为自然立法”的基本含义。马克思哲学相对以往哲学的关键性突破在于, 通过引入“实践”概念, 在后康德的脉络中实现了对康德所开启Deutsche Idealismus的内在批判, 把后者所讨论的意识经验改造为具身行动。因此, 我们对恩格斯所使用的“世界本身”“反映”“唯物”“唯心”等语词, 就绝不能简单地作一种前康德式的理解, 而要超越其字面含义, 把它们理解为后康德式的术语。
上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概念框架在把握康德哲学时的复杂状况, 以及用“唯心主义”这一译名指称康德哲学时的困境, 乃是源于康德哲学本身的复杂性。这里笔者将尝试着对康德思想给出一种复杂的刻画, 以便为后文对马克思与康德开启的“Deutsche Idealismus”之间关系讨论打下基础。
我们先做个康德哲学术语上的处理。“理性”这个词在康德哲学中有多种含义。第一, 理性在最狭窄的意义上指一种追求整全性/通盘把握的能力, 它是理念的来源。第二, 理性在较宽泛的意义上还指一种自发的、主动的综合统一能力, 它的产物包括知性范畴和狭义理性理念。第三, 理性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指康德整个批判哲学所探究的对象, 批判哲学要去探究它的各种先验形式要素及其应用范围。康德分别称这些先验形式要素为感性直观形式、知性范畴、理性理念。不过, 知性范畴又被康德称作纯粹概念;同时, 空间、时间直观形式在很多地方也被康德称作概念;同样地, 理性理念在很多地方也被康德称作概念。基于这一状况, 笔者主张, 我们可以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把理性产生的一切先验形式要素都笼统地称作广义的“理性概念”, 简称为“理念”。相应地, 笔者主张, 我们可以把康德的“Transcendentaler Idealismus”译为“先验理念论”, 把“Deutsche Idealismus”译为“德国理念论”。
笔者的这一翻译主张不同于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西方哲学界以往理解的“德国唯心主义”这一译名, 也不同于目前西方哲学界流行的“德国观念论”这一译名。笔者对前一种译法持保留态度的原因是, 它遮蔽了德国理念论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个问题上的复杂性。笔者反对后一种译法的理由则主要是着眼于康德的先验理念论与柏拉图相论的根本不同。柏拉图的“相”虽不能通过感官之眼“看”到, 但灵魂在实现了“转向”和“飞升”之后就可以直接地“看”到它们。这一点在柏拉图一系列与视觉经验密切相关的寓言、比喻中体现得很清楚。而康德对概念的规定正是通过它与直观的区分作出的, 康德严守的立场是:概念是无法被直观的, 我们无法“看”到概念。从这个角度看, “德国观念论”这一译名就显出其不恰当的地方了, 因为, 该汉译名中的“观”字所暗示的含义正是康德所反对的。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虽然“理念”一词已经被很多学者用来翻译“Idee”这个概念,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赋予它新的含义。在笔者上述的翻译提议中, “理念”乃是“理性自主地产生的先验概念”这一短语的缩略语。此译法试图凸显的是康德开启的德国理念论的三个关键主张: (1) 理性在德国理念论者这里是一种自主的概念生成能力; (2) 理性自主地生成的概念是先验的/纯粹的, 构成了我们现实的认知、行动、情感感受的根据;因此, (3) 先验的理性概念就始终面临着现实化、经验化的问题。
基于上述术语辨析, 我们可以更具体地把康德先验理念论的基本立场表述为:在认识上, 人没有直接通达事物本身的径路, 而是必须透过纯粹理性自主地产生的诸先验形式要素 (理性诸概念) 来感知和思维对象;换言之, 人的认识是理念 (理性概念) 中介的。在实践上, 人也不是像动物一样受着本能的驱使, 而是基于纯粹理性自主地产生的一系列理念和法则来展开行动的;换言之, 人的行动是理念 (理性概念) 指引的。
不过, “先验理念论”只是对康德哲学的一个简化表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 康德多次强调, 他的哲学要从“先验的理念性-经验性的实在性 (die transzendentale Idealitt-die empirische Realitt) ”这两个方面同时把握。
先来看“先验的理念性”。前面, 笔者把“理念”用作“理性自主产生的先验概念”的缩略语。众所周知, “先验”并非简单地指在时间上先于经验。康德承认, 我们的一切知识 (包括概念知识) 都是从经验开始的, 然而, 它们并不全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存在着经验性的概念, 它们在经验中有其根源, 可以被还原为相应的经验;但有些概念是非经验性的、先验的, 它们源于纯粹理性本身, 并构成了经验之可能性的根据。康德称它们是“本源性的 (ursprüngliche) ”, 并据此提出了一种“先验逻辑”的构想, 其任务就是要厘清这些纯粹概念的完备体系。[11]
再来看“经验性的实在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 “实在性 (Realitt) ”作为纯粹知性概念之一, 是与一般感觉相应的东西, “这东西的概念自在地本身表明某种 (时间中的) 存在” (A143/B182) [12]。实在性概念提供了知觉的预测这一纯粹知性的综合原理, 实在的东西一定是具有一个度的感觉对象。因而, 这里的实在性就是指经验性的实在性, 即被现实地经验 (至少可能被现实地经验到) 到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 经验性的实在性可以被等同于现实性。
这样, 先验的理念性刻画的是, 源自理性的 (认识的和实践的) 诸形式要素———理性诸概念 (理念) ———是先验的, 它们无法被还原到经验, 而是构成了经验的根据, 或中介着经验, 或指引着经验;而经验性的实在性刻画的则是, 理性诸概念 (理念) 可以被我们现实地经验到, 而不纯然是思想中的抽象概念。所以, 康德可以说, 经验中的事物就是处于时空中的, 就是具有特定量的, 就是实存的, 就是有属性的, 就是处于因果关系中的, 等等。
要确切地把握康德哲学, “先验的理念性”和“经验性的实在性”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特别地, “先验的理念性-经验性的实在性”中的“-”表示的乃是“既……又……”的并列联结, 而不是表示“要么……要么……”的互斥选择。如果忽视前者, 就会错失康德藉之强调的人作为有理性者的自主本性, 陷入一种经验观念论的立场。如果忽视后者, 就会错失康德藉之强调的人之理性的有限性, 陷入一种先验实在论的立场。
二德国理念论的根本问题:理念现实性的困境
笔者在上文努力表明, 康德哲学乃是一种并非非此即彼的而是更加复杂的“先验理念论-经验实在论”立场, 无法简单地贴上“唯心主义”这一标签。与此有关的一个有趣证据是, 20世纪以塞拉斯为代表的科学实在论者, 从康德这里汲取了关键性的思想资源。他们充分挖掘了康德哲学中“经验性的实在性”这一维度。然而, 康德本人对这一立场却没有贯彻到底, 他把先验的理性诸概念的经验性实在性 (现实性) 构想为不同的状况。
(1) 空间-时间直观形式是“纯直观 (reine Anschauung) ”。虽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后文 (A291/B347) 指出, 纯粹的空间和纯粹的时间虽然作为直观的形式是某物, 本身并不是被直观的对象, 但康德描述的得到纯粹空间、纯粹时间的操作步骤[13]表明, 它们是“先天被给予的” (a priori gegeben) 。空间与时间是直观的形式, 对它们的把握乃是对形式的直观。[14]更重要的是, 空间与时间既然是一切可能经验的构成性先验形式要素, 因此我们就可以现实地经验到, 对象就是处于时空中的。概言之, 空间-时间具有经验性的实在性 (现实性) 。
(2) 纯粹知性概念 (诸范畴) 不同于能在纯粹直观中被给予的空间与时间。前文已经指出, 直观和概念的区分对康德来说是关键性的, 概念是无法被直观的, 因而无法通过发现空间-时间的方式来得出纯粹知性概念。所以, 康德才采取了从判断逻辑机能表推导出范畴表的曲行策略。不过, 与空间、时间一致的是, 纯粹知性概念也是一切可能经验的构成性先验形式要素, 因此我们可以现实地经验到, 对象就是有量的、有质的、处于关系中的、处于特定模态中的。概言之, 诸范畴具有经验性的实在性 (现实性) 。
(3) 狭义的认识理念作为幻相 (der Schein) 区别于现象 (die Erscheinung) , 理念“并不在被直观的对象中 (sind nicht im Gegenstande) ” (A293/B350) 。[15]然而, 一方面, 它作为调节性的原则与经验发生着现实的关系;另一方面, 虽然它作为想象的焦点 (focus imaginarius) 是错觉 (die Tuschung) 、幻觉 (die Illusion) , 但“似乎这些线路是从一个处于可能经验性知识领域之外的对象本身中涌流出来的一样 (如同所看到的客体在镜面背后那样) ” (A644/B672, 这里笔者援引的是梅林的校改文本) 。[16]这句话里的“似乎”“如同”凸显了其错觉性或幻觉性, 但紧接着的文字凸显的是, 它仿佛是处于经验中的, 是在光中显现出来的东西。概言之, 狭义的认识理念虽无经验性的实在性 (现实性) , 但它们是对经验有着合法的调节性作用的自然幻相, 仿佛是现实的。
(4) 自由是狭义行动理念, 康德对它的考察不是在与对象的关系中, 而是在与这个意志及其原因性的关系中展开的。在《实践理性批判》中, 康德强调, 对于这个理性概念 (理念) , 我们“不能作任何经验性描述”, “我们既不能直接意识到自由, ……也不能从经验中推出这概念”。[17]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 康德甚至指出, 虽然我们可以明晰地刻画出于义务所敬重的客观行动法则亦即道德律, 然而, 我们“绝不可能通过经验以完全的确定性澄清任何一个事例, 说其中通常合乎义务的行为仅仅依据道德根据、依据其义务的表象。……即便通过最严格的省察, 也绝不能完全弄清隐秘的动机”。在此, 人们只能看到一个人的行为, 但那行为的内在原则 (自由) 是不为人们看到的。[18]概言之, 自由理念并无丝毫经验性的实在性 (现实性) ,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宣称, 我们现实地经验到了自由。
这一结论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一方面, 它意味着理性内在的分裂:同是源于理性的不同先验形式的要素 (理性诸概念) , 在经验性的实在性上却有着不同的状况。另一方面, 它更意味着理性自身的无能: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据, 其自主产生的诸理念中, 与人的道德行动相关的那个最高的理念———自由“这个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19]———居然没有经验性的实在性 (现实性)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康德曾经尝试过两种方案。我们先看第一个方案。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辨证论”部分讨论“先验的理想”时写道:“先验的肯定则是一个某物, 它的概念自在地本身已经表达了一个存在, 因此被称之为实在性 (事实性) ” (A575/B603) 。[20]在此, 感觉因而时间的要求被取消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 康德进一步发挥了实在性概念的这后一层含义, 从而讨论了自由概念的客观实在性, 以及与自由概念相联结的上帝概念、不朽概念的客观实在性。然而, 对实在性含义的扩展乃是一个糟糕的方案, 因为, 对这些理性概念 (理念) 之实在性的讨论已经不是在讨论其经验性的实在性 (现实性) 。通过扩展实在性的含义, 实际上并不是在解决问题, 而是在取消问题———在扩展了的含义之下, 还有什么没有实在性、不是实在的呢?
因此, 在《判断力批判》中, 康德构想了第二种方案:通过对反思判断力与规定判断力、合目的性与目的性的区别, 重新退回到经验性的实在性 (现实性) 这一根本立场。他讨论了一种特别的现实经验———愉快和不愉快的审美经验, 并具体区分了它的三种类型:优美感受、数学的崇高感受、力学的崇高感受。三者在不同的层次涉及先验理念的现实性问题。
(1) 现实的优美感受乃是由一个被给予的感官对象的某种确定的形式激发的。但这形式乃源于理性概念中的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 它们的经验性的实在性 (现实性) 不仅得到了认知经验的确认, 在此也得到了优美感受的确认。
(2) 数学的崇高涉及“绝对的大”或“无限”理念。无限理念超出了任何感官的尺度, 也就是说, 超出了知性把握的尺度, 因而本不会被经验到, 不具备经验性的实在性。然而, 在数学的崇高感受中, 我们可以在一个直观中直接地把握它。所以康德才说, “自然界在它的这样一些现象中是崇高的, 这些现象的直观带有它们的无限性的理念”。[21]无限性的理念显现 (erscheinen) 在直观之中, 被我们现实地 (审美地) 经验到了。
(3) 力学的崇高同样涉及理性概念 (理念) 。当我们面对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力时, 会激发起我们内心的一种人格性力量, 令我们有勇气与这种强大无比的力量相较量。在力学的崇高感受中, 人的人格性显现出来。而这人格性乃源于理性, 源于人力图根据理性理念———自由———而行动, 力图把它实现出来。如果说, 数学的崇高感受是我们面对无限的对象———比如大海、星空———而产生的一种审美感受, 那么, 力学的崇高感受则无需这一点, 它甚至可以在一个很小的对象———例如, 我们面前的一幅基督受难像———那里被激发。在此, 那作为理性理念的上帝现作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现在就呈现在我的眼前。因而, 在力学的崇高感受中, 理性理念同样显现在了直观中, 同样被我们现实地 (审美地) 经验到了。
康德虽然依旧强调, “要显示概念的实在性永远需要有直观”, 不过, 他根据概念的不同类型区分了直观中显现的类型:经验性概念在直观中的显现是示例 (Beispiel) , 纯粹知性概念在直观中的显现是图形 (Schema) , 理性理念在直观中的显现则是象征 (Symbol) 。象征并不是真地按照直观本身, 即按照所予来处理对象;它对概念的展示是间接的, “是借助于某种 (我们把经验性的直观也应用于其上的) 类比, 在这种类比中判断力完成了双重的任务, 一是把概念应用到一个感性直观的对象上, 二是接着就把那个直观的反思单纯规则应用到一个完全另外的对象上, 前一个对象只是这个对象的象征”[22]。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康德为了解决先验理念的经验性的实在性 (现实性) 问题, 虽然没有采取扩展实在性概念这一方案, 却采取了扩展经验性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直观概念这一方案, 诉诸一种主观的审美感受。
三马克思对德国理念论之根本问题的解决
康德的“先验理念论-经验实在论”面临的根本困境是先验的理性概念的现实性问题。康德哲学的二元论特色正来源于理性的诸概念有着不同的现实性状况。无论是扩展实在性概念的含义, 还是扩展经验性概念的含义, 都无法令人满意。前一种方案企图通过修改概念来取消问题;后一种方案所构想的理念的现实性只是反思判断力视角之下的“仿佛”“似乎”如此, 只是我们基于“自然的合目的性”这个原则的主观想象。
这一不满后来被黑格尔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与那种认为合理东西具有现实性的看法相对立的是这样一种观念, 这种观念既认为理念、理想都只不过是幻想, 哲学是这样一些幻想组成的体系, 又反过来认为理念和理想是某种太卓越无比的东西, 以至于没有现实性, 或同样也是某种太软弱的东西, 以致得不到实现……哲学科学研究的仅仅是理念, 而理念并不是如此软弱无力, 以致只是应当而不是现实的”。[23]在此, 黑格尔面对的康德思想遗产是:理性的内在分裂 (有些理性概念是现实的, 有些理性概念却不是) , 以及理性根本上的软弱无力 (理性无法实现源于自己的概念) 。诚如有些作者所解释的, 康德已经充分揭示了理性的行动本性。在这个意义上, 康德的“科学形而上学”应该被理解为“行而上学”。[24]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康德并没有深入讨论理性的具体行动机制。关于黑格尔与康德思想的关系, 虽然有多种观点, 但主流的观点始终是, 黑格尔是康德哲学遗产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坚定地捍卫康德的先验论主张, 强调思想 (理性概念) 的根本地位, 并更彻底地提出了那个著名的主张:“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在此, 他对康德哲学的关键发展在于, 提出了一种理性概念现实化的自否定-自生成辩证机制。
从康德哲学的角度讲, 理性概念的现实性之所以成为问题, 乃是因为它根本上不是一个分析命题, 而是一个综合命题。在黑格尔看来, 康德对综合判断的构想与传统的形式逻辑学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它们都把判断理解为语词的外在联结, 由此才导致了上述问题。对比之下, 黑格尔的“逻辑学”展示了概念以自否定的方式自生成的机制。[25]在此视域下, 理性概念的现实性问题被转变为, 如何论证理性概念内在地就包括了现实性概念。而这乃是黑格尔“逻辑学”“本质论”部分的重点工作。在那里, 黑格尔基于“映现”的模式, 在与可能、偶然的对应中演绎了现实概念。
众所周知, 黑格尔在此提出的自否定的自生成机制———也就是辩证法———得到了马克思的充分肯定和吸收。然而, 在此, 黑格尔论证的实质是:理性概念内在包含了“现实性”这个概念。从概念上讲, 理性概念是现实的。
至此, 笔者把康德开启的德国理念论根本问题解释为理性概念的现实化问题。在此脉络中, 笔者主张, 马克思可以被视为德国理念论的内在批判者和创造超越者。内在批判者的意思是, 马克思哲学与德国理念论拥有同样的问题视域;创造超越者的意思是, 马克思哲学对德国理念论的问题预设和解决之途作出了全新的构想。
聂锦芳在《Idealismus不是幻想, 而是真理———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一文中注意到了马克思1843年博士论文“题献”里的一句话, “Der Idealismus keine Einbildung, sondern eine Wahrheit ist”。[26]聂锦芳根据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写作和刊布、其主旨和具体论说的深入讨论, 主张不应该把该处的“Idealismus”翻译为“唯心主义”。聂锦芳认为, “从这里可以看出, 长期以来我们对‘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之类哲学范畴的理解是很偏狭的”[27]。不过, 聂锦芳在该文中并没有给出Idealismus的汉译建议。笔者在上文已经提出, 我们可以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Deutsche Idealismus”翻译为德国理念论。而聂文强调, “Idealismus在与物的对立和纠结中把人的价值和意义彰显出来了”[28], 这一合理观点只有放在德国理念论的脉络中才是可理解的。德国理念论始终强调在其开端处康德那里就基于人 (Person) 与物 (Sach) 的区分, 强调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如果说, 在博士论文阶段,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还停留在德国理念论的内部讨论问题, 那么, 马克思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29], 及同年秋至次年春与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特别是讨论费尔巴哈的第一章) [30], 则更明显地体现出他对德国理念论的内在批判和创造超越。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 我们清楚地看到, 马克思所探究的正是“理念的现实性”这个德国理念论的核心问题。对此, 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他把它从一个理论问题转化为一个实践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 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在第八条中, 马克思并非仅仅在说,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物质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他说的是,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第十一条中, 马克思提出, 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 而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只涉及思想, 而改变世界则涉及人凭着理念的指引去行动。
德国理念论的开启者康德的先验哲学有两个基本的预设:第一, “先验/纯粹概念-经验性概念”的严格二分, 以及先验/纯粹概念的奠基性地位;第二, 先验概念框架的唯一性。先验概念框架与人类的经验史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 无论古今中外, 所有有理性者都共享同一套概念框架。黑格尔通过凸显理性作为以自否定的方式自主地生成纯粹概念的能力, 突破了康德的第二个预设, 但他依然接受和保留了康德的第一个预设。
通过引入“实践”概念, 马克思突破了整个德国理念论共有的这个预设, 即“先验的/纯粹的-经验性的”这一二元划分。上述德国理念论的根本问题正是由该划分引发的:由于理性概念是没有任何经验性要素的纯粹概念, 因而理性概念的实现在黑格尔那里只能以概念自身的运动和展开达成。然而, 正如拨动琴弦的不是演奏者的意念, 而只能是演奏者的手指, 同样地, 改变现实事物的, 只能是现实的事物。在马克思这里, 实践成了理念和现实之鸿沟的粘合剂。在实践的视域中, 理念不再是纯然非经验性的东西, 而是现实的物质世界稳定内化的产物;现实也不是偶然随机的东西, 而是理念指引的行动的产物。在实践中理念指引着行为, 在实践中理念得以实现。
通过引入“实践”概念, 引入阶级主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的转变。原先, 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构想, 正如同德国理念论者们所讨论的理念, 始终缺乏切实的现实化路径。现在, 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中基本物质生活运动之内在逻辑的揭示, 通过对历史性的行动主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唤醒, 使共产主义这一思想成为了历史运动的必然的结果。[31]
结语
众所周知, 马克思是通过对德国理念论、特别是对其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而形成自己的哲学主张的。但马克思辩证法的精髓所要求的哲学批判只能是一种内在的批判。在内在批判的视角下, 马克思哲学与以往哲学的关系, 就不能被描述为对以往特定思想的简单接受和杂糅, 从某个哲学家那里继承了一定思想, 从另外一个哲学家那里继承了其他思想。同样地, 我们也不应该过于简单地只突出马克思哲学与德国理念论之间的区别和断裂。内在批判要求我们深入到后者的内部, 探究马克思究竟如何克服其内在的矛盾和困境, 批判性地继承、创造性地超越了后者。
赵敦华在《走向马克思的德国唯心论的“四乐章”》[32]一文中, 把马克思视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出口”。实际上,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著标题里的“Ausgang”, 既有“结尾、尽头”的意思, 也有“开端、起点”的意思。因而, 立于“出口”处的马克思, 可说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开端者, 也是德国理念论的内在批判者和创造超越者:马克思通过引入“实践”, 打破了德国理念论“先验的/纯粹的-经验性的”这个二元对立, 真正解决了德国理念论的根本问题, 即理念的现实性问题。
当然, 笔者在前文已经申明, 本文对德国理念论的刻画尚嫌简单。随着我们对德国理念论的理解越来越丰富, 我们对马克思与德国理念论之关系的讨论也会越来越深入。例如, 德国理念论主张, 作为人的认知和行动之根据的理念, 在性质上乃是纯粹概念, 在来源上乃是纯粹理性通过自否定的辩证机制产生的。马克思是如何从内在批判的角度构想人的理性、理性概念的性质以及理性概念的生成逻辑的?对于德国理念论“先验的/纯粹的-经验性的”严格二分构想, 马克思的方案又是如何不同于简单的还原论, 而是像德国理念论那样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思维和存在、理念和现实之间微妙张力的?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 1990, 第42~45页。
[2]例如, 俞吾金:《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扬弃---兼论马克思的实践、自由概念与康德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俞吾金:《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复旦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徐长福:《马克思主义:从建构性理想到调节性理想---借康德的视角来看》,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徐长福:《先验的自由与经验的自由---以康德和马克思为讨论对象》, 《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王南湜:《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 (上、下) , 《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4、5期;张盾:《康德与黑格尔:谁是马克思的精神源头?》, 《哲学动态》2011年第2期。
[3]例如, 沈真、梁志学:《费希特与马克思》, 《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崔文奎:《费希特的实践概念对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影响》, 《哲学研究》2010年第5期;汤姆·洛克莫尔:《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 东方出版社, 2008;汤姆·洛克莫尔:《马克思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吗?》,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4期。
[4]例如, 参见Frederick Beiser, German Idealism:The Struggle against Subjectiv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下文为了简化表述起见, 笔者将把“德国古典哲学”的所指与“Deutsche Idealismus”的所指简单等同起来, 虽然事实上两者并不完全相同。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第277~286页。
[7]例如, 何中华:《恩格斯对“唯物-唯心”之争的态度---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何中华:《恩格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8]例如, 朱子戟:《论马克思的〈提纲〉与恩格斯的〈终结〉---驳〈提纲〉与〈终结〉“对立论”》,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07年第11期;臧峰宇:《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历史唯物论的阐释---兼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解读》, 《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6期。
[9][12][15][16][2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杨祖陶校, 人民出版社, 2004, 第203页;第142页;第259页;第507页;第460页。
[10]参见亨利·阿利森:《康德的先验观念论》, 丁三东、陈虎平译, 商务印书馆, 2015, 第2至4章。
[11]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参见丁三东:《康德对纯粹概念完备体系的构想》, 《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3]从一个物体的表象出发, 首先把知性凭借其概念所想到的东西除开, 只留下经验性的直观;然后从这个经验性的直观中再把一切属于感觉的东西除开, 最终余留下来的就是空间-时间。
[14]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杨祖陶校, 人民出版社, 2004, “先验感性论”部分。对此问题的深入讨论参见阿里森:《康德的先验观念论》, 丁三东、陈虎平译, 商务印书馆, 2015, 第110~115、151~155页。
[17][19]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人民出版社, 2003, 第16、38页;第2页。
[18]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李秋零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第23~24页。
[21][22]康德:《判断力批判》, 邓晓芒译、杨祖陶校,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94页;第199页。
[23]黑格尔:《哲学百科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 梁志学译,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37~38页, 另请参见该书第264~265页。
[24]例如, 邓安庆:《启蒙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德国古典哲学的道德事业之重审》, 人民出版社, 2014, 第80~99页。
[25]具体论说参见丁三东:《黑格尔思辨逻辑中的判断学说》, 《云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丁三东:《自由的逻辑---康德背景下的黑格尔逻辑学定位》, 《哲学研究》2016年第12期。
[26]笔者根据本文的翻译主张, 把这句话译为:“理念论不是幻想, 而是真理”。
[27][28]聂锦芳:《Idealismus不是幻想, 而是真理---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29][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31]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末尾说, “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在此, 他正是以隐晦的方式点出了德国理念论的根本缺陷, 即理念缺乏现实化的真正行动力量。
[32]赵敦华:《走向马克思的德国唯心论的“四乐章”》,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3期。
(原载《哲学动态》2017年第10期)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 电话:(010)85195506
电话:(010)85195506
![]() 传真:(010)65137826
传真:(010)65137826
![]()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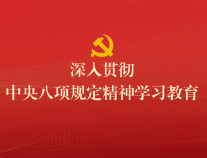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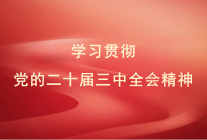




 潘梓年
潘梓年 金岳霖
金岳霖 贺麟
贺麟 杜任之
杜任之 容肇祖
容肇祖 沈有鼎
沈有鼎 巫白慧
巫白慧 杨一之
杨一之 徐崇温
徐崇温 陈筠泉
陈筠泉 姚介厚
姚介厚 李景源
李景源 赵汀阳
赵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