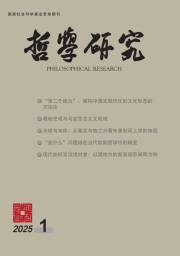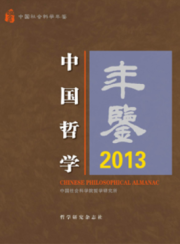首页
首页-
本所概况
哲学所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 党建工作
- 研究学人
- 科研工作
- 学术期刊
- 人才培养
博士后更多+
- 图书档案
图书馆简介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 - 哲学系
【陈静】《<中国哲学史>四十年文选》序

《中国哲学史》四十年文选(全五卷)
主编:陈来、李存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出版
接到刘丰电话,嘱我为《<中国哲学史>四十年文选》写几句话,略感意外。毕竟,我离开《中国哲学史》编辑部已经5年,是他们策划选编了《中国哲学史》建刊以来的论文,以五个主题分别成集。现在文集即将付梓,吾亦何德何能,敢来饶舌多嘴!刘丰说编辑部的同事没有忘记我也曾为这个杂志服务,诚恳希望我与他们一道,分享文集问世的喜悦。这份念旧的情谊令我感动。确实,我们曾经一起为这个杂志喜,为这个杂志忧,为这个杂志劳作,为这个杂志奔走,在这个愉快的时刻他们想到我,愿意我的笑声应和他们的欢语,这让我感动。但是,撰写庄重序言实非吾能,只能记几则旧事,杂忆也罢,随想也罢,就是它吧。
一、羞惭。我刚刚参加《中国哲学史》的编辑时,这个杂志还处于“散漫”状态。所谓“散漫”,是指没有稳定的编辑部,也没有专职编辑;没有可靠的经费来源,更没有程序化的管理。几位老师在本职的研究工作之余,义务地编辑着这本季刊。稿源有限,有什么稿,就编什么稿。我参与编辑,也是抓着便帮忙做一点,抓不着便逃之夭夭,自我逍遥。工作也简单,就是让那些写在方格稿纸上的文章变成铅字,再改正排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字。那时还是手写稿多,也有一些打印文稿,现在通行的电子文本和电子排版,那时还未出现。我被告知可以改动原稿,调整表述什么的,但是除了改正笔误的错字,我从来不改别人的文章。我不喜欢别人动我的文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也从不改订别人的文章。要用便用,不用就退,有修改意见就告知作者,如果作者愿意接受,自己去改,我决不会以己之意,改彼之文。可以说,这个态度贯穿了我的整个编辑工作。
由于没有稳定的经费,杂志的印制费用时时难以为继。我那时年轻,这份烦忧还不关我事,只是有一次蒙培元先生去广州筹款,让我一起去,我才多少了解了这本杂志的艰难。
冯达文老师帮助我们以编辑部的名义开了一个座谈会。原本是为筹款而去,但既然开会,就不好意思只是说钱。介绍情况之后,也请与会老师给编辑部提意见和建议,没有说出口的话则是希望有人认捐,或者提供筹款渠道。会上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有一位年轻老师的话让我记忆深刻。他问如果捐款是否就可以发表文章。因为蒙先生让我主持会议,所以我回答可以有优先权,但编辑部要保留文章的终审权。也许是穷到讨米下锅我还绷着的态度实在不讨喜,那位年轻人脱口而出,说《中国哲学史》编得很差,“别处发不出的文章我们才给《中哲史》呢!”他这样说。我觉得自己脸涨红了。我知道他说的并非全是气话,我也听人转述过某海外作者的抱怨,说删除他文章的注释是“太没有水平了”。在我冒汗脸红的那一刻我暗下决心,以后要更积极些,如果由我主事,一定要改变《中国哲学史》在同行心目中的形象。三十多年过去了,在编辑部同事的共同努力下,我想我们基本做到了。现在,《中国哲学史》作为本研究领域的专业刊物,获得了它的声誉。
二、尴尬。广州之行,最后是冯达文老师和吴重庆先生合力筹措了一笔资金,才让那一期杂志顺利印行,帮助编辑部渡过了难关。后来,刘笑敢先生在新加坡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找到了资助,陈来先生也在哈佛-燕京学社联系到了资助,再加上杂志发行的回款和合作栏目的资助,编辑部渐渐摆脱了窘境。我也曾经向某基金会的负责人争取资助,旁观我说项的一位朋友事后劝我算了,“你做不了这事儿,那种场合根本不合适谈这个,可是你不懂”。朋友这样说。通过别人的眼睛,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用功是多么可笑。那些年,我们的尴尬往往与钱有关,与经费的获得有关,也与经费的使用有关。当时,一些小印厂取费相对低廉,如果不要求正式发票,还可以更少一点。我向时任会长的任继愈先生汇报情况,他笑曰“一个穷学会,怎么办呢?能省就省吧。”他信任我们,相信我们不会乱花钱,更不会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编辑部内部也逐渐建立管理制度,钱款由学会保管,编辑部取用和支出则分人负责。再后来,整个社会的财会制度越来越规范,编辑部的财务改由哲学所代管,一切财务往来都通过银行。虽然运作的费用因此提高了,却也避免了多心人猜疑的眼光。毕竟,我们不可能把账本挂在脖子上,让愿意查验的人随时翻看。我们自信是干干净净的人,但是制度才让我们无懈可击。就我们的经验而言,制度确实比人品更容易获得信任,更能够抵挡流言蜚语。
与钱相关的尴尬还有诈骗。曾经有人利用《中国哲学史》在网上行骗,以允诺发表收取费用。等有人致电编辑部催促发表,我们才发现名义被盗用了。报警后警方似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不知是不是由于涉案金额太小的缘故。我们只好自己在杂志上刊登不收取版面费的声明,提醒作者不要上当。而某位上当者坚持认为骗局有编辑部内部的人参与,我告诉他我了解每一位参与编辑的人,“此事决无可能”,终究没有改变他的看法,只能随他去。《中国哲学史》即使在经费最困难的情况下,也不出卖版面并拒绝刊登广告。合作办栏目,也强调保留稿件的终审权。我们的一切努力,只在保持这个刊物的学术水准,和它作为一个学术刊物应有的严肃风格,即使遭遇各种尴尬,亦不改初衷。因为这个杂志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学科的知识,还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传统,她需要我们以真诚和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三、宗旨。我刚刚接手杂志的日常工作时,曾经请示学会会长任继愈先生,《中国哲学史》当以什么为宗旨。“当然是发表这个领域最好的成果。”任先生回答。我继续请问,我们是否要像梁山好汉一样,扯一面杏黄大旗,上书“中国哲学最高明”之类的口号以为号召,或者像陈鼓应先生办《道家文化研究》主张“道家主干说”那样,也有一个主干的主张?“哦”,任先生明白了我的问题,他想了一下,回答说:“还是发表这个领域最好的成果吧。”这些年来,《中国哲学史》真的是更多追踪学术界的研究,虽然也会顺势推动一些话题,但从不刻意主张什么,尤其不会观点先行地主张什么。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热爱自己的传统;作为长期浸淫于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我们也有自己的研究偏好和立场观点,但是,我们并不以自己为尺度来定取舍,而是以“发表这个领域最好的研究成果”为追求。《中国哲学史》不是一个阵地,而是一个平台,一个展示学术研究进展和趋势的平台。当四十年过去,选捡不同主题的论文汇编成册,中国哲学史研究这四十年来的整体风貌就展示出了它的大致格局。
四、反省。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一度笼罩在哲学教科书所规划的理解架构下。以一个思想家的阶级出身来为他的思想定位,询问他的思想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方法是辩证的还是形而上学等,曾经是研究的基本格套。由于并未切中思想者自己的问题和其思想的真实理路以及学术传承脉络,研究在表面的正确之下显得空洞而不切实际,动辄批判的态度也在透显着无知的虚妄。后来风气渐渐改变,教科书的框架被放弃了,但是外在规范的习惯似乎还保留着,只不过眼光从教科书改变成为各种时新的思想流派。20世纪90 年代以后,又有所谓思想淡出而学术凸显的改变,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更加深入自身的历史脉络和内在理路的探索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似乎更多是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的,是从更加准确、深入、丰富并同情理解曾经的思想上获得的,而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面,尚无实质进展。试图以历史性描述来充当普遍性逻辑,还是相当多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的自由、民主、法制等,还未能从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出发获得充分的理论论证。自由以承认个人权利为逻辑前提,而中国思想传统并不重视权利,也没有个人的观念;由于没有个人的观念,中国传统思想甚至没有“幸福”的观念。中国哲学史研究能够继续忽视权利的个人吗?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从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中敞开这些方面的内容,在我看来还是理论上的很大的困难。我一直为此苦恼,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后来者。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也将有远大的未来,在理论的困境中我虽然苦恼,却仍然乐观地相信未来。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1.11.10)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 电话:(010)85195506
电话:(010)85195506
![]() 传真:(010)65137826
传真:(010)65137826
![]()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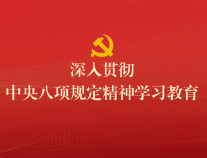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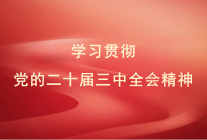



 潘梓年
潘梓年 金岳霖
金岳霖 贺麟
贺麟 杜任之
杜任之 容肇祖
容肇祖 沈有鼎
沈有鼎 巫白慧
巫白慧 杨一之
杨一之 徐崇温
徐崇温 陈筠泉
陈筠泉 姚介厚
姚介厚 李景源
李景源 赵汀阳
赵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