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一】“回到你自己”——苏赫拉瓦尔迪论在场认知
摘要:在场认知,是国际学界苏赫拉瓦尔迪及中世纪阿拉伯照明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学者的解读存在很大分歧。本文基于三个关键阿拉伯语文本,系统重构在场认知理论,证明它并非一种神秘主义知识论,而是一种哲学认识论——认知的本质,是认知客体对非物质主体的在场。在场认知的提出,是为了取代伊本·西那(阿维森纳)的形式认知理论,以求解决人类如何认知殊相事物以及神如何认知殊相事物的难题,此外更构成整个照明哲学的认识论根基。苏赫拉瓦尔迪坚信人类认知的合适对象是殊相而非共相,照明学派的终极追求是以在场的方式直接认知殊相万物,尤其是对神和众分离理智的 “精神性观测” 。
关键词:苏赫拉瓦尔迪;伊本·西那(阿维森纳);照明哲学;认识论;在场认知
一、引言
在场认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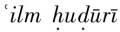 , presential knowledge)是国际学界苏赫拉瓦尔迪(Suhrawardī,1154-1191,中世纪阿拉伯照明学派创始人)及其照明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学者对于如何解读这一理论存在很大分歧。科尔班(H.Corbin)、纳斯尔(S.H.Nasr)和艾敏拉扎维(M.Aminrazavi)等人持神秘主义立场(cf.Corbin,pp.205-220;Nasr,pp.52-82;Aminrazavi,pp.78-120),认为它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理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和升华至一种神秘主义类型的知识,此种知识要超越通常被称为‘哲学的’领域”。(Kaukua,2013,p.309)然而,这种神秘主义解读忽视了在场认知理论的哲学本质,导致无法揭示出其真正的哲学价值和哲学史意义。近期,艾希纳(H.Eichner)和考库瓦(J.Kaukua)等学者开始关注在场认知理论背后的哲学动机和语境,亦即12至13世纪伊斯兰东部哲学家对伊本·西那(Ibn Sīnā,拉丁名“阿维森纳”Avicenna,970-1037,中世纪阿拉伯逍遥学派集大成者)哲学的批判性接受。艾希纳认为,在场认知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伊本·西那认识论中的身心关系难题;考库瓦反驳艾希纳的解读,认为苏赫拉瓦尔迪意图解决的难题是神如何认知殊相事物(
, presential knowledge)是国际学界苏赫拉瓦尔迪(Suhrawardī,1154-1191,中世纪阿拉伯照明学派创始人)及其照明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学者对于如何解读这一理论存在很大分歧。科尔班(H.Corbin)、纳斯尔(S.H.Nasr)和艾敏拉扎维(M.Aminrazavi)等人持神秘主义立场(cf.Corbin,pp.205-220;Nasr,pp.52-82;Aminrazavi,pp.78-120),认为它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理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和升华至一种神秘主义类型的知识,此种知识要超越通常被称为‘哲学的’领域”。(Kaukua,2013,p.309)然而,这种神秘主义解读忽视了在场认知理论的哲学本质,导致无法揭示出其真正的哲学价值和哲学史意义。近期,艾希纳(H.Eichner)和考库瓦(J.Kaukua)等学者开始关注在场认知理论背后的哲学动机和语境,亦即12至13世纪伊斯兰东部哲学家对伊本·西那(Ibn Sīnā,拉丁名“阿维森纳”Avicenna,970-1037,中世纪阿拉伯逍遥学派集大成者)哲学的批判性接受。艾希纳认为,在场认知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伊本·西那认识论中的身心关系难题;考库瓦反驳艾希纳的解读,认为苏赫拉瓦尔迪意图解决的难题是神如何认知殊相事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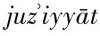 , particulars)。(cf. Eichner; Kaukua, 2013; 2015, pp. 125-142)
, particulars)。(cf. Eichner; Kaukua, 2013; 2015, pp. 125-142)
本文旨在将在场认知理论去神秘化:它并非一种神秘主义知识论,而是一种哲学认识论。在场认知是苏赫拉瓦尔迪对认知本质的原创解说——认知(idrāk,apprehension),是认知客体对非物质主体的在场( ,presence);以取代伊本·西那所构建的形式认知(
,presence);以取代伊本·西那所构建的形式认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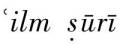 , formal knowledge)理论——认知,是认知客体的形式在主体中的发生(
, formal knowledge)理论——认知,是认知客体的形式在主体中的发生( , occurring)或印记(
, occurring)或印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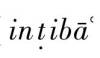 , imprinting)。具体而言,在场认知理论的提出,首先是为了解释人类认知的本质,尤其是人类如何认知殊相事物;其次是为了解释神的认知,尤其是神如何认知殊相事物。尽管在场认知最终会升华为某种“神秘”知识,但这可以得到合理的哲学阐释。苏赫拉瓦尔迪坚信人类认知的合适对象是殊相而非共相(kulliyyāt, universals)。因此,照明学派的终极追求,是突破人类认知局限,通过在场的方式,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所有现实殊相事物,不仅包括这个世界之中的物质性殊相,也包括这个世界之外的非物质殊相,即神和众分离理智。对于后者的在场认知,即是苏非主义中所谓的精神性的“直观”(mushāhada, witnessing)、“品尝”(dhawq, tasting)和“揭示”(kashf/mukāshafa, unveiling)。此外,本文还会证明在场认知理论,正是苏赫拉瓦尔迪整个照明哲学的认识论根基。
, imprinting)。具体而言,在场认知理论的提出,首先是为了解释人类认知的本质,尤其是人类如何认知殊相事物;其次是为了解释神的认知,尤其是神如何认知殊相事物。尽管在场认知最终会升华为某种“神秘”知识,但这可以得到合理的哲学阐释。苏赫拉瓦尔迪坚信人类认知的合适对象是殊相而非共相(kulliyyāt, universals)。因此,照明学派的终极追求,是突破人类认知局限,通过在场的方式,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所有现实殊相事物,不仅包括这个世界之中的物质性殊相,也包括这个世界之外的非物质殊相,即神和众分离理智。对于后者的在场认知,即是苏非主义中所谓的精神性的“直观”(mushāhada, witnessing)、“品尝”(dhawq, tasting)和“揭示”(kashf/mukāshafa, unveiling)。此外,本文还会证明在场认知理论,正是苏赫拉瓦尔迪整个照明哲学的认识论根基。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本文重点考察三部分阿拉伯语文本。(1)苏赫拉瓦尔迪在第一本逍遥学派风格著作《天牌与王座之指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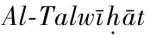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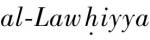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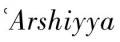 )的形而上学部分III.1“论认知和非物质性”中,首次提出在场认知理论,通过详细记录一段他与亚里士多德[页下注:此处“亚里士多德”的所指存疑,或许是《亚里士多德神学》(The Theology of Aristotle)中的“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普罗提诺。《亚里士多德神学》是阿拉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奠基作之一,它事实上是对普罗提诺《九章集》IV-VI的节选和改写,后被归于亚里士多德。(cf. Adamson)]在梦境中关于认知本质的对话。(cf. Suhrawardī, 1993a, pp.70-74)(2)随后在其长篇逍遥学派风格著作《源头与论辩》(
)的形而上学部分III.1“论认知和非物质性”中,首次提出在场认知理论,通过详细记录一段他与亚里士多德[页下注:此处“亚里士多德”的所指存疑,或许是《亚里士多德神学》(The Theology of Aristotle)中的“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普罗提诺。《亚里士多德神学》是阿拉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奠基作之一,它事实上是对普罗提诺《九章集》IV-VI的节选和改写,后被归于亚里士多德。(cf. Adamson)]在梦境中关于认知本质的对话。(cf. Suhrawardī, 1993a, pp.70-74)(2)随后在其长篇逍遥学派风格著作《源头与论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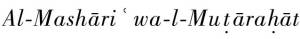 )的形而上学部分VII.1“论认知和知识”中,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在场认知理论。(cf. Suhrawardī, 1993b, pp483-489)(3)此外,相关讨论也分散出现在其照明主义集大成著作《照明哲学》(
)的形而上学部分VII.1“论认知和知识”中,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在场认知理论。(cf. Suhrawardī, 1993b, pp483-489)(3)此外,相关讨论也分散出现在其照明主义集大成著作《照明哲学》( Ishrāq)中。(cf. Suhrawardī, 1993c,1999)本文将首先简要梳理在场认知理论的哲学语境,随后基于上述阿拉伯语文本系统重构该理论,最后揭示照明哲学的本质以及在场认知理论的哲学史意义。
Ishrāq)中。(cf. Suhrawardī, 1993c,1999)本文将首先简要梳理在场认知理论的哲学语境,随后基于上述阿拉伯语文本系统重构该理论,最后揭示照明哲学的本质以及在场认知理论的哲学史意义。
二、在场认知理论的语境
在场认知理论的哲学语境,是12至13世纪伊斯兰东部哲学家对于伊本·西那关于认知本质之解说以及对其整个认识论的普遍不满。这种不满不仅见于苏赫拉瓦尔迪,也见于同期其他重要哲学家和神学家,如艾布·巴拉卡特·巴格达迪(Abūl-Barakāt al-Baghdādī,约1080-1165)以及著名神学家法赫尔丁·拉齐(Fakhr al-Dīn alRāzī,1149-1210,曾与苏赫拉瓦尔迪是同窗)。(cf. Benevich, 2020; Rāzī, pp.219.2-233.13)
(一)伊本·西那形式认知理论的难题
在《拯救书》(AlNajāt)中,伊本·西那说:“似乎每种认知,的确都是对认知对象形式( , form)的获取。”(Ibn Sīnā, 1985, p.344.3)换言之,认知,是认知对象形式的发生或印记,这便是形式认知理论的要旨。然而,苏赫拉瓦尔迪认为伊本·西那的形式认知理论至少面临如下两个难题。
, form)的获取。”(Ibn Sīnā, 1985, p.344.3)换言之,认知,是认知对象形式的发生或印记,这便是形式认知理论的要旨。然而,苏赫拉瓦尔迪认为伊本·西那的形式认知理论至少面临如下两个难题。
第一,形式认知无法适用于所有人类认知。苏赫拉瓦尔迪论证到,至少有四种人类认知无法通过形式认知来解释,分别是自我认知、对身体及其诸种官能的认知、对截肢疼痛的认知以及视觉。这些认知均无需通过任何形式。事实上,这些认知的发生都是因为认知对象本身的在场(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第二,形式认知无法有效解释人类对殊相事物的认知。根据伊本·西那,人的灵魂在本性上是理智( , intellect),所以其合适的认知对象应是共相。但人的灵魂同时控制着身体及其诸种官能,并与物质世界交互;因此,我们也能够认知殊相事物,尽管只能“以共相的方式”(
, intellect),所以其合适的认知对象应是共相。但人的灵魂同时控制着身体及其诸种官能,并与物质世界交互;因此,我们也能够认知殊相事物,尽管只能“以共相的方式”( wajh kullī, in a universal way)。在正式引入在场认知理论前,苏赫拉瓦尔迪首先概述了伊本·西那的解决方案及其面对的困难:
wajh kullī, in a universal way)。在正式引入在场认知理论前,苏赫拉瓦尔迪首先概述了伊本·西那的解决方案及其面对的困难:
要知道,允许灵魂以共相的方式认知诸殊相事物。比如,灵魂将宰德认识为那高的、黑色的和某人之子,就那些共相不同时聚集在他者之中而言。但尽管如此,那些共相的集合,其内涵自身并不阻止对它的共有(al-sharika, sharing)的发生。如果共有的不可能性被设想了,那是因为并非此内涵的阻碍。让这一点在你那里成为一条规则吧。(Suhrawardī, 1993a, p.69.12-15)
尽管苏赫拉瓦尔迪接受伊本·西那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对应的共相形式来认知殊相事物,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认知能够精确反映殊相事物本身。因为没有任何形式(无论是单一形式还是诸多形式的集合)能够通过其自身阻止对它的共有;但每个殊相事物却都通过其自身阻止对它的共有。举例而言,我确实能够以共相的方式认知宰德,将他认知为诸多共相的集合,比如“高的、黑色的和某人之子”。但同时,允许现实中有其他人共有“高的、黑色的和某人之子”这些共相的集合,比如宰德的兄弟;除非已知宰德是独生,但这已构成“并非此(共相集合)内涵的阻碍”,而此共相集合的内涵自身并不阻止多者对它的共有。另一方面,我也能够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宰德,将他认知为独一无二的殊相个体,而形式认知却无法解释后一种认知。
与伊本·西那相反,苏赫拉瓦尔迪相信人类认知的合适对象事实上是殊相,而并非共相。人类能够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殊相事物,而不仅仅是以共相的方式或通过共相形式。
(二)以伊本·西那的原初自我意识理论作为起点
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难题,苏赫拉瓦尔迪从“自我认知”(al-idrāk lil-dhāt, self-apprehension)出发。他在《天牌与王座之指示》中写到,自己曾被知识(alilm, knowledge)的难题困扰许久而不得答案,直到亚里士多德在梦境中与他展开一段对话。在对话伊始,亚里士多德建议道:“回到你自己( ilā nafsika,return to yourself),则(知识的难题)就会为你解开。”(Suhrawardī, 1993a, p.70.7)苏赫拉瓦尔迪由此清晰地意识到,至少有一个殊相事物,即每个人的自我,是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必须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的。以自我认知为起点,他进一步论证到:除了自我,人类一定能够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更多殊相事物。事实上,殊相而非共相,才是人类认知的合适对象(详见本文第三、四部分)。
ilā nafsika,return to yourself),则(知识的难题)就会为你解开。”(Suhrawardī, 1993a, p.70.7)苏赫拉瓦尔迪由此清晰地意识到,至少有一个殊相事物,即每个人的自我,是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必须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的。以自我认知为起点,他进一步论证到:除了自我,人类一定能够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更多殊相事物。事实上,殊相而非共相,才是人类认知的合适对象(详见本文第三、四部分)。
此处必须提及的是,苏赫拉瓦尔迪所讨论的“自我认知”,事实上是伊本·西那的认识论洞见。(cf. Kobayashi; Marcotte; Kaukua, 2011)近些年,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伊本·西那的“(原初)自我意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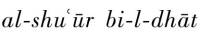 , [primitive] self-awareness)这一概念的重要性。(cf. Black; Kaukua, 2015)然而,伊本·西那的原初自我意识,却与其形式认知理论难以相容,下面做一简要分析。
, [primitive] self-awareness)这一概念的重要性。(cf. Black; Kaukua, 2015)然而,伊本·西那的原初自我意识,却与其形式认知理论难以相容,下面做一简要分析。
在《治疗书·论灵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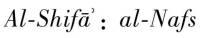 )著名的“飞人实验”[页下注:伊本·西那的“飞人实验”是阿拉伯哲学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实验之一,要旨如下:在一瞬间被造、拥有完整的身体和理智、但缺失任何认知对象(除了其自我)的、悬浮在空气中的“飞人”,仍然能够且仅仅能够确定其自我(dhāt, self)的存在,但他无法同时确定自己的身体或任何外界事物的存在。飞人实验起初用以论证自我(即人的灵魂)的非物质性,后来用以揭示原初自我意识现象。(参见张天一,2024年)]中,伊本·西那首次提出原初自我意识这一重要认识论现象(cf. Ibn Sīnā, 1959, pp.15.19-16.17),但对其的详细阐述是在后期著作中展开的。伊本·西那在《注释》(Al-
)著名的“飞人实验”[页下注:伊本·西那的“飞人实验”是阿拉伯哲学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实验之一,要旨如下:在一瞬间被造、拥有完整的身体和理智、但缺失任何认知对象(除了其自我)的、悬浮在空气中的“飞人”,仍然能够且仅仅能够确定其自我(dhāt, self)的存在,但他无法同时确定自己的身体或任何外界事物的存在。飞人实验起初用以论证自我(即人的灵魂)的非物质性,后来用以揭示原初自我意识现象。(参见张天一,2024年)]中,伊本·西那首次提出原初自我意识这一重要认识论现象(cf. Ibn Sīnā, 1959, pp.15.19-16.17),但对其的详细阐述是在后期著作中展开的。伊本·西那在《注释》(Al-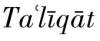 )中指出:原初自我意识是本己性的(dhātī)、无中介的(
)中指出:原初自我意识是本己性的(dhātī)、无中介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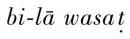 )、无限定的(
)、无限定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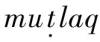 )和无条件的(
)和无条件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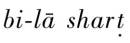 )以及恒常的(
)以及恒常的( )。(cf. Ibn Sīnā, 2013b, p.481.4-7)根据《提示与提醒》(
)。(cf. Ibn Sīnā, 2013b, p.481.4-7)根据《提示与提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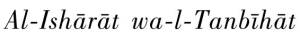 ),一个人即便在睡眠、醉酒和假想的“飞人”状态下,依然拥有原初自我意识。(cf. Ibn Sīnā, 2013a, p.233)事实上,每个人的自我的形成,正是因为原初自我意识,所以原初自我意识构成一个人一切知行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没有正在意识着自我,他也就不会成为一个自我、一个“我”。打个比方,原初自我意识就像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运行的最基本的“后台程序”,它如此根本和普遍,并且几乎总是与其他认知混杂在一起,因此我们通常不会特别注意到自己的原初自我意识。伊本·西那所设计的飞人实验,正是“调出原初自我意识后台程序”的方式之一。通过排除自我之外的所有其他认知对象,飞人实验迫使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原初自我意识本身。
),一个人即便在睡眠、醉酒和假想的“飞人”状态下,依然拥有原初自我意识。(cf. Ibn Sīnā, 2013a, p.233)事实上,每个人的自我的形成,正是因为原初自我意识,所以原初自我意识构成一个人一切知行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没有正在意识着自我,他也就不会成为一个自我、一个“我”。打个比方,原初自我意识就像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运行的最基本的“后台程序”,它如此根本和普遍,并且几乎总是与其他认知混杂在一起,因此我们通常不会特别注意到自己的原初自我意识。伊本·西那所设计的飞人实验,正是“调出原初自我意识后台程序”的方式之一。通过排除自我之外的所有其他认知对象,飞人实验迫使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原初自我意识本身。
可见,原初自我意识不涉及任何形式,因而与伊本·西那的形式认知理论难以相容。苏赫拉瓦尔迪则从原初自我意识出发,构建新的在场认知理论,不但进一步开发伊本·西那这一认识论洞见的哲学潜力,更旨在为人类认知的本质提出新的哲学解释。下面,本文将基于相关阿拉伯语文本,系统重构在场认知理论。
三、构建在场认知理论
作为构建在场认知理论的第一步,苏赫拉瓦尔迪试图证明:至少有四种人类认知无需通过任何形式,而是仅需认知对象本身的在场。这四种认知分别是自我认知、对身体及其诸种官能的认知、对截肢疼痛的认知以及视觉。
(一)自我认知
苏赫拉瓦尔迪首先证明,自我认知无需任何形式。在相关文本中可以找到三个论证,本文分别称其为“殊相性论证”“我性论证”和“在先性论证”。
(1)殊相性论证分别出现在《天牌与王座之指示》和《源头与论辩》中,要旨如下:既然每个形式,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共相性的(即不阻止对其自身的共有)[页下注:苏赫拉瓦尔迪称“每个在灵魂中的形式都是共相性的”(Suhrawardī,1993a,p.70.12),这是“共相”一词的宽泛用法,指每个形式通过其自身都不阻止对它的共有。这一用法区别于伊本·西那共相理论中对于“共相”一词的严格用法。(cf. lbn Sīnā,2012,pp.195-212)],但每个人的自我都是殊相性的(即阻止对其自身的共有);因此,自我认知不可能通过任何形式。否则,对于一个共相的认知,就将等同于对于一个殊相的认知,而这是荒谬的。(cf. Suhrawardī, 1993a, pp.70.9-71.4; 1993b, p.484.10-14)
(2)我性论证分别出现在《源头与论辩》和《照明哲学》中,要旨如下:既然每个形式,对于人的灵魂而言都是一个“它”(huwa),也就是某个不同于灵魂自身的东西;但灵魂的自我,对于灵魂而言却是那个“我”(anā),也就是灵魂自身;因此,自我认知不可能通过任何形式。否则,不同于灵魂的东西,就将等同于灵魂自身,而这是荒谬的。(cf. Suhrawardī, 1993b, p.484.7-10; 1993c, p.111.5-9, §115)
(3)在先性论证仅出现在《照明哲学》中,要旨如下:每个自我认知者,都必先认知其自我,而后才能认知到某物是与其自我相符的形式。比如,如果我知道A是与我相符的形式,那么我必须事先已经认知了我的自我(不附带A),而后才能认知到A是与我相符的。否则,如果我没有事先认知我的自我,我怎会知道A与我相符?若如此,A将与我不相关,那么我即便认知了A,也不会通过A认知到我的自我。因此,我不可能通过任何形式,来认知我的自我。(cf. Suhrawardī, 1993c, p.111.9-14, §115)
基于上述三个论证,苏赫拉瓦尔迪得出:自我认知不可能通过任何形式,而是仅需自我本身的在场。
(二)其他三种在场认知
关于其他三种在场认知的论证,本文仅作简要介绍。首先,对身体及其诸种官能的认知,不可能是形式认知。此论证分别出现在《天牌与王座之指示》和《源头与论辩》中,思路与上文关于自我认知的“殊相性论证”一致。既然每个形式,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共相性的(即不阻止对其自身的共有),但每个人的身体及其诸种官能都是殊相性的(因为无法设想我的身体或任何官能同时属于他人)。因此,对于身体及其诸种官能的认知,不可能通过形式。(cf. Suhrawardī, 1993a, p.715-17; 1993b, pp.484.14-485.6)
随后,仅在《源头与论辩》中,苏赫拉瓦尔迪还考察了一种对截肢疼痛的认知。假设某人的肢体被截断,那么他会感觉到疼痛并拥有对此疼痛的认知。然而,他的认知不应是因为某个形式发生在截断处或身体其他部位。因为他显然失去了肢体,同时并没有获得任何东西。如果设想他在这种状态下还获得了某个形式,似乎是荒谬的。(cf. Suhrawardī, 1993b, p.485.7-12)
最后,分别在《源头与论辩》和《照明哲学》中,苏赫拉瓦尔迪还论证到,视觉也不可能是形式认知。(cf. Suhrawardī, 1993b, pp.485.13-486.17; 1993c, pp.99.15-101.12, §101-103)根据伊本·西那,视觉的发生是因为外物的形式印记在晶状体上。但苏赫拉瓦尔迪质疑到:比如我看见一座大山,而大山的量(miqdār, magnitude,即大小)是属于其形式的,“那么这巨大的量如何发生在微小的眼球中?”(Suhrawardī, 1993c, p1008-9, §102)苏赫拉瓦尔迪得出:“视觉仅仅就是被照亮的事物与视觉器官的相遇(muqābala)。”(Suhrawardī, 1993b, p.486.15)
既然对截肢疼痛的感觉和视觉都不属于形式认知,那么可以推测,苏赫拉瓦尔迪似乎认为所有外感觉(视听嗅味触)都不是形式认知,而是在场认知。
(三)在场,作为人类所有认知的本质
在论证上述四种认知都不属于形式认知后,苏赫拉瓦尔迪在《天牌与王座之指示》和《源头与论辩》中指出:人类所有认知的本质,都是认知客体对主体的在场。(cf. Suhrawardī, 1993a, pp.71.18-72.12; 1993b, p.487.6-17)
如果你已经知道,灵魂认知,既不通过符合的印象也不通过形式;那么你要知道,理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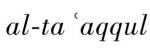 , understanding)就是事物对非物质自我的在场。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说,(理解就是)事物对于非物质自我的不缺席(
, understanding)就是事物对非物质自我的在场。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说,(理解就是)事物对于非物质自我的不缺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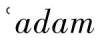 ghayba, non-absence)。(Suhrawardī, 1993a, pp.71.18-72.2)
ghayba, non-absence)。(Suhrawardī, 1993a, pp.71.18-72.2)
从引文中可以提取出关于认知的两个条件:认知客体对主体的在场(或称不缺席)以及认知主体的非物质性(tajarrud, immateriality)。
首先考虑“在场”(或称不缺席)这个条件。苏赫拉瓦尔迪之所以附加“不缺席”,是因为在自我认知中,说我的自我对于我“在场”是不精确的。因为只有A和B是两个不同事物时,才能说A对于B在场(或B对于A在场)。但我和我的自我并不是两个不同事物,而是完全同一的;所以在自我认知中,只能说我的自我“不缺席”于我。因此,“不缺席”事实上是“在场”的一种更精确说法。但作为哲学术语,苏赫拉瓦尔迪仍宽泛地使用“在场”一词。[页下注:值得一提的是,伊本·西那在讨论原初自我意识时,已使用“在场”一词。比如他在《注释》中说:“自我在任何状态下都在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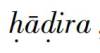 , present)于自我。”(Ibn Sīnā, 2013b, p.442.11)苏赫拉瓦尔迪使用“在场”一词,很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伊本·西那的影响。]
, present)于自我。”(Ibn Sīnā, 2013b, p.442.11)苏赫拉瓦尔迪使用“在场”一词,很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伊本·西那的影响。]
“非物质性”条件,来自于苏赫拉瓦尔迪关于人的灵魂(即自我)的非物质性的诸多论证。大致跟随伊本·西那,比如在《天牌与王座之指示》的物理学中,苏赫拉瓦尔迪共提出三组论证来证明人的灵魂的非物质性,其中就包括对伊本·西那飞人实验的改述。(cf. Suhrawardī, 2009, pp155.17-157.16, pp.163.8-166.3)
随后,苏赫拉瓦尔迪进一步通过“在场”这一概念,来统合在场认知和逍遥学派所主张的形式认知。
如果灵魂不能使一个事物本身在场,比如天空和大地等,它就使得其形式在场。殊相事物,(灵魂使其形式)在诸官能(即想象官能)中在场,而这些官能对于灵魂在场;而共相,则是在其自我(dhāt)中(在场),因为在认知对象中,有无法印记在形体中的诸共相。(Suhrawardī, 1993a, p.72.4-7)
现实殊相事物首先可分为两类:在灵魂中在场的事物和在灵魂中缺席的事物。如果一物在场,那么灵魂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它,无需通过任何形式。此时获取的认知,就称为“在场认知”,如上文分析过的四种在场认知。如果一物在灵魂中缺席,那么灵魂就要使其形式在场,并通过其形式来认知它。此时获取的认知,就称为“形式认知”。缺席的事物可以再分为两类:殊相和共相。如果缺席的是殊相事物,比如关羽的赤兔马,灵魂就要使其形式在场于想象官能,从而认知它。如果缺席的是共相,比如“马”这个种,灵魂就要使其共相形式在场于其自我,从而认知它。
由此可见,无论在场认知还是形式认知,在根本上都是认知对象的“在场”。在场认知中,在场的是现实殊相事物本身;而形式认知中,在场的则是缺席的殊相事物的可想象形式,或可理解的共相形式。由此,苏赫拉瓦尔迪利用“在场”统合了两种认知。此外,苏赫拉瓦尔迪显然认为在场认知比形式认知更为优越、更高等。因为只有当我们无法使得现实殊相事物本身在场时(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才需要诉诸形式;一旦这些殊相事物在场,我们便不再需要其形式,而是能够直接地在场认知它们。(cf. Suhrawardī, 1993b, p.487.9-12)
(四)在场认知,作为神的知识
通过提出在场认知,苏赫拉瓦尔迪不仅旨在解释人类认知的本质,还旨在解释神的认知。(cf. Suhrawardī, 1993a, pp.72.13-73.7; 1993b, pp.486.18-488.12)既然对于人类而言,在场认知要优越于形式认知,并且鉴于神要远比人类完满,那么神的认知必是在场性的。苏赫拉瓦尔迪写道:
如果(如下这一点)是正确的:照明主义知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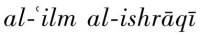 )不通过形式或印象,而是仅通过一种特殊的关系(
)不通过形式或印象,而是仅通过一种特殊的关系( , relation),亦即,事物通过照明主义方式的在场,正如对于灵魂那样;那么对于其存在必然者(wājib al-wujūd, that whose existence is necessary)[页下注:“其存在必然者”(wājib al-wujūd)是伊本·西那的形而上学术语,指就其“存在”(wujūd, existence)而言,是必然的东西,也就是神。除神以外的所有造物,都是“其存在可能者”(mumkin al-wujūd, that whose existence is contingent)。]而言,(这种认知)就是更合适和更完全的。(Suhrawardī, 1993b, p.487.2-4)
, relation),亦即,事物通过照明主义方式的在场,正如对于灵魂那样;那么对于其存在必然者(wājib al-wujūd, that whose existence is necessary)[页下注:“其存在必然者”(wājib al-wujūd)是伊本·西那的形而上学术语,指就其“存在”(wujūd, existence)而言,是必然的东西,也就是神。除神以外的所有造物,都是“其存在可能者”(mumkin al-wujūd, that whose existence is contingent)。]而言,(这种认知)就是更合适和更完全的。(Suhrawardī, 1993b, p.487.2-4)
根据伊本·西那《治疗书·形而上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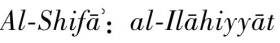 )VIII.6,神在本性上是理智,其认知对象应是共相;因此神不能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殊相事物,而是只能“以共相的方式”(
)VIII.6,神在本性上是理智,其认知对象应是共相;因此神不能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殊相事物,而是只能“以共相的方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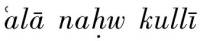 , in a universal manner)。此外,鉴于殊相事物殊多且不断变化,而伊本·西那认为认知是形式的发生或印记,所以关于殊相事物的认知会造成殊多和变化的形式发生在神的本己(dhāt,即自我)之中,从而威胁神的单一性和不变性。(cf. Ibn Sīnā, 2012, pp.358.14-362.11; Marmura)后来,伊本·西那关于神之认知的论点受到神学家安萨里(Al-Ghazālī,约1056-1111)在《哲学家的矛盾》(Tahāfut al-Falāsifa)中的著名批判。(cf. Ghazālī, pp.134-143)苏赫拉瓦尔迪构建在场认知理论的主要哲学动机之一,正是为了解决神如何认知殊相事物的难题。根据苏赫拉瓦尔迪,神的合适认知对象不应是共相而是殊相事物,因此神当然可以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殊相事物,而并非“以共相的方式”。其次,鉴于“在场”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关系”,那么殊相事物的殊多和变化,仅会导致神与殊相事物之间“关系”的殊多和变化,这并不会威胁神自身的单一性和不变性。(cf. Benevich, 2019)苏赫拉瓦尔迪论证到:“理智关系(
, in a universal manner)。此外,鉴于殊相事物殊多且不断变化,而伊本·西那认为认知是形式的发生或印记,所以关于殊相事物的认知会造成殊多和变化的形式发生在神的本己(dhāt,即自我)之中,从而威胁神的单一性和不变性。(cf. Ibn Sīnā, 2012, pp.358.14-362.11; Marmura)后来,伊本·西那关于神之认知的论点受到神学家安萨里(Al-Ghazālī,约1056-1111)在《哲学家的矛盾》(Tahāfut al-Falāsifa)中的著名批判。(cf. Ghazālī, pp.134-143)苏赫拉瓦尔迪构建在场认知理论的主要哲学动机之一,正是为了解决神如何认知殊相事物的难题。根据苏赫拉瓦尔迪,神的合适认知对象不应是共相而是殊相事物,因此神当然可以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殊相事物,而并非“以共相的方式”。其次,鉴于“在场”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关系”,那么殊相事物的殊多和变化,仅会导致神与殊相事物之间“关系”的殊多和变化,这并不会威胁神自身的单一性和不变性。(cf. Benevich, 2019)苏赫拉瓦尔迪论证到:“理智关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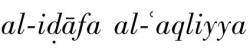 )的繁多性不会要求它(即神的)本己(dhāt)中的殊多性。”(Suhrawardī, 1993c, p.153.3-4, §162)“如果它(即神)的知识是在场性照明性的,不通过在其本己中的形式;那么如果某物消失,比如说,而关系(al-
)的繁多性不会要求它(即神的)本己(dhāt)中的殊多性。”(Suhrawardī, 1993c, p.153.3-4, §162)“如果它(即神)的知识是在场性照明性的,不通过在其本己中的形式;那么如果某物消失,比如说,而关系(al- )消失,并不导致它自身之中的变化。”(Suhrawardī, 1993b, p.488.3-4)
)消失,并不导致它自身之中的变化。”(Suhrawardī, 1993b, p.488.3-4)
四、照明主义知识的等级
尽管苏赫拉瓦尔迪并未在相关文本中明确阐述照明主义框架内的知识等级,但上文关于在场认知的分析已经揭示出等级的存在。神的在场认知优越于人类的在场认知;而人类的在场认知也有高低之分,比如自我认知要优越于对身体及其诸种官能的认知,而后者又优越于诸种外感觉。
最高级在场认知,可称为“本原性统制性在场认知”,鉴于苏赫拉瓦尔迪将神与其认知对象之间的关系称为一种“本原性统制性关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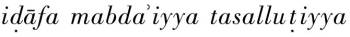 )。(cf. Suhrawardī, 1993a, p.72.16)在最高级在场认知中,认知主体是客体的“本原”(
)。(cf. Suhrawardī, 1993a, p.72.16)在最高级在场认知中,认知主体是客体的“本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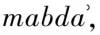 principle),也就是说客体的存在与否完全依靠主体;换言之,认知主体对于客体拥有一种“统制”(
principle),也就是说客体的存在与否完全依靠主体;换言之,认知主体对于客体拥有一种“统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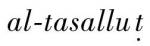 , total dominion)。(cf.Suhrawardī, 1993b, p.487.18)正是由于这种“统制”,认知客体恒常在场于主体。苏赫拉瓦尔迪以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作类比:我们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会因为这种“控制”(
, total dominion)。(cf.Suhrawardī, 1993b, p.487.18)正是由于这种“统制”,认知客体恒常在场于主体。苏赫拉瓦尔迪以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作类比:我们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会因为这种“控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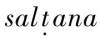 , dominion)而在场于我们;而神作为万物本原对于万物拥有“统制”,远比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更完满,所以万物恒常在场于神。(cf. Suhrawardī, 1993a, p.73.5-6)因此,在最高级在场认知中,客体永远无法逃离主体的认知,而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也永远无法被剥夺(除非客体消失)。神对于万物的在场认知,属于此最高级别;而在神之下的众分离理智,对于在它们之下的所有事物也拥有此种最高级在场认知。自我认知也应属于最高级在场认知,因为自我认知也是恒常的、无法被剥夺的。但区别在于我和我的自我之间的关系不是本原性或统制性的,而是一种完全同一的关系。苏赫拉瓦尔迪说:“你的自我就是理解、理解者和理解对象。”(Suhrawardī,1993a,p.71.3-4)也就是说,在自我认知中,认知主体、客体和认知本身,三者同一。
, dominion)而在场于我们;而神作为万物本原对于万物拥有“统制”,远比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更完满,所以万物恒常在场于神。(cf. Suhrawardī, 1993a, p.73.5-6)因此,在最高级在场认知中,客体永远无法逃离主体的认知,而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也永远无法被剥夺(除非客体消失)。神对于万物的在场认知,属于此最高级别;而在神之下的众分离理智,对于在它们之下的所有事物也拥有此种最高级在场认知。自我认知也应属于最高级在场认知,因为自我认知也是恒常的、无法被剥夺的。但区别在于我和我的自我之间的关系不是本原性或统制性的,而是一种完全同一的关系。苏赫拉瓦尔迪说:“你的自我就是理解、理解者和理解对象。”(Suhrawardī,1993a,p.71.3-4)也就是说,在自我认知中,认知主体、客体和认知本身,三者同一。
第二级在场认知,可称为“控制性在场认知”,示例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及其诸种官能的在场认知。在此级别中,尽管认知主体不是客体的本原,但仍对客体拥有一种控制(但不拥有统制),所以客体会因为这种控制而在场于主体。一旦控制消失,认知主体就会失去对于客体的在场认知,比如被截肢者无疑会失去对其肢体的在场认知。
第三级也是最低级的在场认知,是我们对于外界可感殊相事物的在场感觉。在感觉中,认知主体既不是客体的本原,也不对客体拥有统制或控制;感觉的发生,仅仅是因为认知主体相应感官与客体的“相遇”(muqābala)。根据苏赫拉瓦尔迪,感觉的发生机制如下:首先,认知主体对其诸种感官拥有控制,从而拥有对其感官的第二级在场认知;当认知主体的感官与客体相遇时,客体便以感官为媒介在场于主体。因此,第三级在场认知与第一、二级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需要感官作为媒介;第一、二级在场认知则无需任何媒介。在感觉中,认知主体可以轻易失去对客体的在场感觉。因为只要客体不再在场,甚至即便客体在场但只要主体没有“注意”(iltifāt)客体,比如“视而不见”这种常见现象,主体就会失去对客体的感觉。(cf. Suhrawardī, 1993b, p.485.13-18)
根据苏赫拉瓦尔迪,逍遥学派所关注的形式认知,要低于上述三个等级的在场认知。因为形式认知的对象,已不是现实殊相事物本身,而是它们的形式,或是可想象形式(如赤兔马的形式),或是可理解共相形式(如“马”这个种的共相形式)。需再次强调的是,只有当我们无法使得现实殊相事物本身在场时(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我们才需要通过它们的形式来认知它们。再者,在场认知是直接的、如其所是的、动态的、全面的;相比之下,形式认知则是间接的、共相性的、静态的、相对片面的。
五、照明学派追求的终极在场认知
此时我们不禁要问:苏赫拉瓦尔迪所追求的在场认知,难道仅是这样一些杂乱的、彼此不甚相关的认知和感知?我们将如何通过这些认知,构建起对世界的整体哲学认知?如果不系统重构《照明哲学》中的光之形而上学,无法详尽解答这一难题。本文仅简要描述照明学派所追求的终极在场认知究竟为何物。正是在此时,在场认知会升华为某种“神秘”知识,苏赫拉瓦尔迪称之为对神和众分离理智的“精神性观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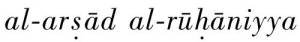 , spiritual observations)(Suhrawardī, 1993c, p.156.8, §165),可参考对于天体的天文学观测;同时,这也就是苏非主义中常说的精神性“直观”“品尝”和“揭示”。这里看似“神秘”的在场认知事实上并不神秘,可以在苏赫拉瓦尔迪的在场认知理论中得到合理的哲学阐释。
, spiritual observations)(Suhrawardī, 1993c, p.156.8, §165),可参考对于天体的天文学观测;同时,这也就是苏非主义中常说的精神性“直观”“品尝”和“揭示”。这里看似“神秘”的在场认知事实上并不神秘,可以在苏赫拉瓦尔迪的在场认知理论中得到合理的哲学阐释。
根据上文分析,神拥有最高级在场认知,即本原性统制性在场认知。在此种认知中,所有事物,包括神的自我,都同时对神在场。也就是说,神连同其自我同时一并认知和把握所有事物,一瞬间构建起对世界的整体认知,并且神会通晓其中每个最微小的细节。苏赫拉瓦尔迪写道:
如果我们对于并非我们身体的事物,也有控制,正如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那样;那么我们也会像认知身体那样认知其他事物,根据上文所述,而无需形式。(Suhrawardī, 1993a, p.73.5-6)
这里,苏赫拉瓦尔迪从人对自己身体的认知(即第二级在场认知)出发,设想神的最高级在场认知。假设我们不仅控制着自己的身体,同时也控制周遭的一切事物,如桌子、书本、墙壁,甚至每一粒尘埃;那么我们就会像认知自己的身体那样,以一种更高级的、在场的方式认知周遭一切事物,通晓它们的每个细节。神的最高级在场认知大致如此,但还要更加完满;因为神拥有作为万物本原的绝对“统制”,而不仅仅是“控制”。除了神,也称“万光之光”(nūr al-anwār, Light of lights),超越此世界的非物质光界之中的众分离理智皆是如此,它们在光之形而上学中称为“征服性非物质光”(al-anwār al-mujarrada al-qāhira, conquering immaterial lights),它们全都对它们之下的所有事物拥有本原性统制性在场认知。
照明学派的终极追求,即是这种最高级在场认知,而并非第二、三级在场认知。事实上,只有当一个人摆脱身体(进而也摆脱第二、三级在场认知),才有可能获得最高级在场认知,通过上升至非物质光界,参与光界高等非物质光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照明(ishrāq)和直观(mushāhada),征服(qahr)和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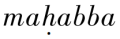 )或渴求(
)或渴求( )。苏赫拉瓦尔迪写道:
)。苏赫拉瓦尔迪写道:
一束低等光,如果在它和一束高等光之间没有阻隔(h·ijāb),低等光就会直观高等光,而高等光之光则会照明于低等光。(Suhrawardī, 1993c, p.133.14-15, §143)
在光之形而上学中,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一束“非物质光”(nūr mujarrad, immaterial light)。非物质光,即是自我认知者(al-mudrik lil-dhāt, self-apprehender),包括每个人的灵魂、天体灵魂、非物质光界的众分离理智以及唯一的神。(参见沙宗平、王希)当一个人的灵魂、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自我认知的自我、一束非物质光,摆脱身体并上升至非物质光界时,它与众多更高等非物质光(即众分离理智和神)之间将不再有阻隔。因此,灵魂将能够在场认知、直观、品尝和揭示那些高等非物质光,从而分有它们所拥有的对殊相万物的最高级在场认知。通过这种方式,人类就能够通过最高级在场认知,构建起对世界的最精确、最完全的哲学认知。
六、结语
在《照明哲学》前言中,苏赫拉瓦尔迪写道:
这是另一条途径和路径,比那种(逍遥学派的)方法更简短、更有序、更精确,并且更容易获得。它起初并不是通过思考(al-fikr)而发生于我的;而是,它的发生是通过其他方式。随后,我寻求对于它的证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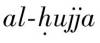 ),直到即便比如我停止对于证明的考察,也无人能令我怀疑它。(Suhrawardī, 1993c, p.10.8-10, §3)
),直到即便比如我停止对于证明的考察,也无人能令我怀疑它。(Suhrawardī, 1993c, p.10.8-10, §3)
苏赫拉瓦尔迪所谓的“另一条途径和路径”无疑指的就是在场认知。在场认知总是关于现实殊相事物本身的,所以它“更精确”。在场认知无需借助概念、定义、判断或论证,而是仅需认知对象本身的在场;在这个意义上,它相比于形式认知会“更简短”“更有序”“更容易获得”,并且不通过“思考”而发生。此外,在场认知无需逻辑证明,并且不会令人生疑。由此可见,在场认知理论正是整个照明哲学的认识论根基。苏赫拉瓦尔迪坚信人类认知的合适对象是殊相而非共相;因此,他的理想在于尝试打破人类认知的枷锁,通过在场的方式直接地、如其所是地认知殊相万物,尤其是对神和众分离理智的“精神性观测”。
必须强调的是,苏赫拉瓦尔迪在提出这种超理性在场认知的同时,从未否定理性的形式认知的合法性。事实上,绝大多数人无法达到这种超理性认知,所以理性认知仍是人类获取知识的最普遍途径。苏赫拉瓦尔迪相信,理性形式认知和超理性在场认知事实上殊途同归,最终应到达一种同样的哲学,它应是唯名论和存在主义的。但伊本·西那哲学中存在对理性认知的多处误用,故而得出的是一种实在论和本质主义的哲学。(参见张天一,2023年b)苏赫拉瓦尔迪构建照明哲学正是旨在纠正这些谬误,最终达到理性认知和超理性认知二者的融合统一。这也正是苏赫拉瓦尔迪的照明哲学既区别于伊本·西那主义,也区别于苏非主义之处。(参见张天一,2023年a)
关于苏赫拉瓦尔迪的在场认知理论及其照明哲学,国际学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评判。如井筒俊彦(T. Izutsu)认为,苏赫拉瓦尔迪开创了伊斯兰哲学的新纪元,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哲学是“神秘主义经验与分析性思辨的完美融合”。(cf. Izutsu, pp.59-62)相似地,纳斯尔主张:“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哲学,并没有随阿维罗伊(即伊本·鲁世德)终结,而是在他逝世后才真正开始,随着苏赫拉瓦尔迪的学说开始在伊斯兰东部土壤上散布。”(Nasr, p.56)相反地,古塔斯(D. Gutas)则认为,安萨里和苏赫拉瓦尔迪共同将“一种超理性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引入阿拉伯哲学,这是“在阿维森纳之后伊斯兰的反科学发展”。(cf. Gutas, p.36)本文主张搁置上述立场,客观地评估苏赫拉瓦尔迪在场认知理论的哲学价值和哲学史意义。首先,在阿拉伯哲学中一直被忽视的自我意识或称自我认知现象(伊本·西那虽有分析但仍缺乏系统性),在在场认知理论中首次得到系统分析和阐述。其次,在场认知理论揭示出苏赫拉瓦尔迪强烈的唯名论倾向,区别于伊本·西那的实在论,这为后伊本·西那传统开辟出新的发展方向。第三,这一理论为苏非主义认识论提供合理的哲学解释,使其成为哲学探究的合法工具。最后,这一理论在阿拉伯哲学史上影响深刻而深远,在苏赫拉瓦尔迪之后,伊斯兰东部的阿拉伯哲学正在逐步脱离亚里士多德传统,变得愈发独立。
【参考文献】
[1]沙宗平、王希,2014年:《简论苏赫拉瓦迪的照明哲学》,载《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
[2]张天一,2023年a:《论苏赫拉瓦尔迪的照明主义计划与照明哲学的本质》,载《犹太研究》第22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23年b:《苏赫拉瓦尔迪论心智思虑物——从唯名论存在主义角度批判存在与本质的现实区分》,载《哲学动态》第2期。
2024年:《伊本·西那的飞人论证和原初自我意识的通透性》,载《世界哲学》第2期。
[3]Adamson,P.,2021,“The Theology of Aristotle”,in E.Zalta(ed.),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Fall 2021 Edition),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21/entries/theology-aristotle/.
[4]Aminrazavi,M.,1997,Suhrawardi and the School of Illumination,London:Curzon Press.
[5]Benevich,F.,2019,“God's Knowledge of Particulars:Avicenna,Kalām,and the Post.Avicennian Synthesis”,in Recherches de Théologie et Philosophie Médiévales 86(1).
2020,“Perceiving Things in Themselves:Abūl.Barakāt al.Bag·dādī's Critique of Representationalism”,in Arabic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0(2).
[6]Black,D.L.,2008,“Avicenna on Self-Awareness and Knowing that One Knows”,in S.Rahman et al.(eds.),The Unity of Science in the Arabic Tradition,Dordrecht:Springer.
[7]Corbin,H.,1993,History of Islamic Philosophy,L.Sherrard and P.Sherrard(trans.),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8]Eichner,H.,2011,“‘Knowledge by Presence’,Apperception and the Mind.Body Relationship:Fakhr al-Dīn al-Rāzīand al-Suhrawardīas Representatives and Precursors of a ThirteenthCentury Discussion”,in P.Adamson(ed.),In the Age of Averroes:Arabic Philosophy in the Sixth/Twelfth Century,London:The Warburg Institute.
[9]Ghazālī,Al-,2000,The Incoherence of the Philosophers,M.E.Marmura(trans.),Provo,Utah: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ess.
[10]Gutas,D.,2018,“Avicenna and After:The Development of Paraphilosophy.A History of Science Approach”,in A.Al Ghouz(ed.),Islamic Philosophy from the 12th to the 14th Century,Bonn:Bonn University Press.
[11]Ibn Sīnā,1959,Avicenna's De Anima(Arabic Text):Being the Psychological Part of Kitāb al-Shifā',F.Rahman(e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Al-Najāt min al-Gharaq f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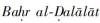 ,M.T.Dānishpazhūh(ed.),Tehran:Dānishgāh-i Tihrān.
,M.T.Dānishpazhūh(ed.),Tehran:Dānishgāh-i Tihrān.
2012 ,Al-Shifā:al-Ilāhiyyāt,I.Madkūr et al,(eds.),Qom: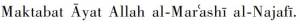
2013a,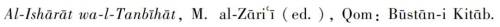 2013b,
2013b, ,SaHMousavian(ed,),Tehran:Irani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aHMousavian(ed,),Tehran:Irani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12]Izutsu,T.,1971,The Concept and Reality of Existence,Tokyo:The Keio Institute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
[13]Kaukua,J.,2011,“I in the Light of God:Selfhood and Self-Awareness in Suhrawardī'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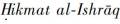 ”,in P.Adamson(ed.),In the Age of Averroes:Arabic Philosophy in the Sixth/Twelfth Century,London:The Warburg Institute.
”,in P.Adamson(ed.),In the Age of Averroes:Arabic Philosophy in the Sixth/Twelfth Century,London:The Warburg Institute.
2013,“Suhrawardī's Knowledge as Presence in Context”,in Studia Orientalia 114.
2015,Self-Awareness in Islamic Philosophy:Avicenna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Kobayashi,H.,1990,“Ibn Sīnāand Suhrawardīon SelfConsciousness:Some Comparative Remarks”,in Orient 26.
[15]Marcotte,R.D.,200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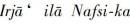 :Suhrawardī's Apperception of the Self in Light of Avicenna”,in Transcendent Philosophy 1.
:Suhrawardī's Apperception of the Self in Light of Avicenna”,in Transcendent Philosophy 1.
[16]Marmura,M.E.,1962,“Some Aspects of Avicenna's Theory of God's Knowledge of Particulars”,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2(3).
[17]Nasr,S.H.,1997,Three Muslim Sages: Avicenna.Suhrawardī-Ibn‘Arabī, Delmar, New York: Caravan Books.
[18]Rāzī,Fakhr al-Dīn,200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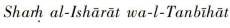 ,vol.2,A.R.Najafzādah(ed.),Tehran:Anjuman.ithār va Mafākhir.i Farhangī.
,vol.2,A.R.Najafzādah(ed.),Tehran:Anjuman.ithār va Mafākhir.i Farhangī.
[19]Suhrawardī,1993a,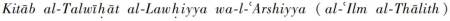 ,in H.Corbin(ed.), Œuvres Philosophiques et Mystiques(Tome I),Tehran:Institut d'Etudes et des Recherches Culturelles.
,in H.Corbin(ed.), Œuvres Philosophiques et Mystiques(Tome I),Tehran:Institut d'Etudes et des Recherches Culturelles.
1993b,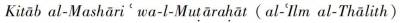 K,in H.Corbin(ed.), Œuvres Philosophiques et Mystiques(Tome I),Tehran:Institut d'Etudes et des Recherches Culturelles.
K,in H.Corbin(ed.), Œuvres Philosophiques et Mystiques(Tome I),Tehran:Institut d'Etudes et des Recherches Culturelles.
1993c,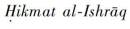 ,in HCorbin(ed.), Œuvres Philosophiques et Mystiques(Tome II),Tehran:Institut d'Etudes et des Recherches Culturelles.
,in HCorbin(ed.), Œuvres Philosophiques et Mystiques(Tome II),Tehran:Institut d'Etudes et des Recherches Culturelles.
1999,The Philosophy of Illumination,J.Walbridge and H.Ziai(trans.),Provo,Utah: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Tehran:Irani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Tehran:Irani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原载:《哲学研究》2025年第1期
来源:哲学研究公众号2025年3月22日
















 潘梓年
潘梓年 金岳霖
金岳霖 贺麟
贺麟 杜任之
杜任之 容肇祖
容肇祖 沈有鼎
沈有鼎 巫白慧
巫白慧 杨一之
杨一之 徐崇温
徐崇温 陈筠泉
陈筠泉 姚介厚
姚介厚 李景源
李景源 赵汀阳
赵汀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