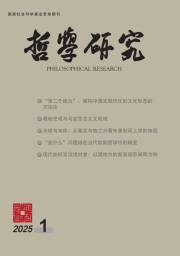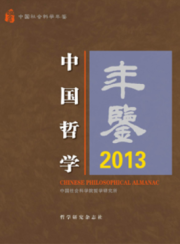【卢春红】从“原真性”到“可技术复制性”:艺术何以成为媒介?
1935—1939年间,处于流亡期间的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完成了美学名篇《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的写作。对于这一主题,作者前后写过三稿,结构大同小异,内容各有侧重。在本雅明的写作生涯中,这部“作为《拱廊街》的当代补充而被构思和写作”的著作能够成为其学术思想的代表性成果,固然在于该部著作以光晕的消失为切入点,呈现艺术存在由传统到现代的变化过程,更在于本雅明对现代艺术的敏锐感受,并以肯定性的态度预见了以“可技术复制性”为核心的媒介艺术“潜在的结构性特征”。从当代的视角反观,本雅明对这一特质的描述虽相对简缩,却依旧给我们领会现时代的艺术存在带来多重启发,本文尝试以艺术与媒介的关联为内在线索,展开分析本雅明对可技术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定位所具有的深层意义。
一、“原真性”与“可技术复制性”:光晕何以消失?
虽然本雅明对传统艺术之特质的分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从《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的总体思路来看,作者的关注重心在现代艺术,传统艺术是作为阐明现代艺术的参照背景而呈现的。1839年,法国摄影师路易斯·达盖尔发明银版摄影法,使得摄影艺术开始了自身的探索过程。1895年,法国的路易·卢米埃尔兄弟正式公映自己制作的几部短片,标志着电影艺术时代的到来。如果说前者还在对传统绘画“图像”的借鉴与区分中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后者则通过“影像”的动态化展示而彰显自身的独立性。将这一过程推进至20世纪80年代,数字化技术更是给艺术作品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本雅明未能看到数字化时代的现实效应,但在19世纪30年代的生活世界中,“可技术复制”已日渐成为现代艺术的主导性存在方式。本雅明敏锐地感受到伴随技术革新而来的艺术存在的本质性变化,一方面通过1931年的《摄影小史》阐明摄影的出现对于艺术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此后的《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以电影为代表,通过对照进一步揭示出现代艺术的内在特质。由这一总体诉求反观传统艺术时,本雅明以原真性为切入点分析了光晕何以标志着传统艺术的总体特征。
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首先对“原真性”做了如下界定:“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从这一界定可看出,将传统艺术的特点指向“原真性”,依托的是作为创作之原初形态的“原作”,并与产生于模仿的复制品形成对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为了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而生产复制品,并通过技术手段来提高复制水平,从文字的印刷到声音图片的复制,体现的是复制技术的推进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复制品虽依附于原作,并因为原作而获得自身的存在,却也具有独立存在的现实意义。不过,认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复制品可以代替原作。强调原作与复制品的区分,表明即使复制品已达到严格意义上的仿真程度,也只是对原作在形式上的摹写,并不能呈现其本质风貌。正如本雅明所强调,“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einmaliges Dasein)”。
可见,“即时即地性”是关键因素。它之所以能呈现出作品的原真性,在于其首先通过“即时即地性”让艺术作品成为原作,复制品缺乏的正是这一特点。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一即时即地性?通过与“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相关联可知,“即时即地性”指向的其实是原作所独有的“起源”问题。早在1925年的授职论文《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本雅明就将“原真之物(Das Echte)”视为“现象中的起源(Ursprung)印记”,并对“起源”做了如下解释:“在每一个起源现象中,都会确立形态,在这个形态之下会有一个理念反复与历史世界发生对峙,直到理念在其历史的整体性中实现完满。”指出起源现象中的理念因素,表明这一起源并不是某部具体艺术作品的产生,而是艺术作为一般存在的创建与开启,因为正是理性使得原作拥有了成为开启者的依据。不过,单纯的理念并不能真正开启一段“独一无二”的存在,须得将这一因素融入艺术作品之中。即时即地性的意义由此彰显:通过此时此刻,理念得以进入作品,也真正开启作品之作品存在。纯粹的理性与精神并不涉及“此时此地”的存在,古代思想将艺术称作对“应当存在的事物”的模仿,强化的正是理念的视角。只有当神圣性东西真正开始接纳感性,并以感性的方式呈现时,当下性才因神圣性因素的融入显示出自身的特殊意义。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进一步指出,“一件东西的原真性包括它自问世那一刻起可继承的所有东西,包括它实际存在时间的长短以及它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证据”,意在强调原作对于艺术存在之历史性的开启。
如果原作意味着历史性的开启,那么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理念以何种方式进入艺术作品。这就涉及本雅明的另一个重要术语——光晕(Aura)。从词源学角度,术语Aura由其拉丁文演变而来,并从一开始就具有“光”与“神秘性”两层内涵。不过,本雅明将其作为核心概念的意图则在于:如果说理念是历史过程的开启因素,那么光晕则是这一因素在艺术作品中的直接显现。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也对“光晕”概念做了如下简洁描述:“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显然,指出光晕“在一定距离之外”,强调的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距离,虽然本雅明声称是从时空角度描述这一概念,但这里的时空显然是在隐喻意义上使用,暗含的是所显现之物对于现实生活而言的外在性,因为它呈现的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传统”,拥有的是可让我们膜拜的神圣性。之所以“感觉上如此贴近”,亦非是指时空意义上的近,而是意图表明这一传统并不是绝对与我们无关的,它可以直接出现在作品之中,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并由此显示出与当下存在的内在关联。在这一意义上,本雅明指出“一件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性是与它置身于其中的传统关联相一致的”,则是从艺术作品的角度强调了二者的直接关联性。使艺术作品拥有独一无二性的是现身于作品中的传统,而传统产生这一独一无二性的标志被本雅明称作“光晕”。换言之,正是通过这一直接结合,艺术在获得自身的独一无二性之时,也使得作品拥有了神圣的光晕。
由对原真性的关注而引出传统艺术所内含的光晕,目的是由此切入现代艺术。本雅明认为,现时代的艺术与传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即是,艺术作品中的光晕不复存在。他将这一变化的缘由归结为技术的引入,是技术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如果说传统艺术是以艺术家为主导的创作方式,那么现代艺术则更多依赖于技术制作,并因此造成艺术作品的“可技术复制性(technische Reproduzierbarkeit)”。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的现象是,在对传统艺术的分析中,原作是以与复制品对峙的身份出现,并且是复制品所无法替代的,而在面对现代艺术时,原作的身份似乎明显弱化,关注的重心转向通过“可技术复制性”而产生的复制品。不可否认,在以技术为主要生产模式的现代艺术中,复制品的生产规模较之于传统的复制模式显著扩大,本雅明对这一生产模式下的复制品投入较多关注并不意外。由此认为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中,原作与复制品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传统艺术中,复制品相对于原作处于从属地位,而在现代艺术中,复制品的存在方式一跃而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停留于表面现象的误导。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由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复制作品地位的升降,而是在这一变革中作品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前者呈现的只是表象,后者揭示的则是本质。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不具有“开启”意义的复制品均无法替代原作。因而,如果传统艺术中以原作方式呈现的艺术作品具有独一无二性,那么在现代艺术中,真正发生改变的则是原作的存在方式。
反思现代艺术的制作过程,技术操作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消除原作在此时此地的感性存在。从本质上讲,艺术作品不只是以理念为其依据,更需要以感性方式呈现自身,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性正是通过可感性而彰显。与此相对照,无论是以底片或者胶片方式存在的早期摄影和电影作品,还是后来以数字化方式存在的艺术作品,其共同特点都是以非感性方式制作艺术。这源于技术的理性本质。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指出,“技术就是具有一种真正理性的创制品质”,强调了技术作为创制的内在依据——与理性的本质关联。将艺术称作技艺,所要剥离的无疑是艺术的感性品质。现代艺术将技术操作引入创作过程,也因此在自身中置入一种潜在的意图。一旦这一技术占据主导地位,拥有自身承担艺术存在的独立性,势必会导致原作的不可感。
对于现代艺术而言,正是通过这一方式,原作才真正拥有可复制性。在传统艺术中,原作能够拥有自身的独一无二性,在于这一艺术进入存在的方式始终是感性的,由此它才能让自身呈现出神圣的光晕,在这一意义上,传统艺术中的原作本质上是无法复制的。现代艺术想要拥有自身的可复制性,首先需要摆脱的便是艺术作品的这一感性存在方式。引入技术制作的关键之处正在于,使原作的存在方式由感性存在转变为非感性存在。但这并非说,原作就此不复存在,原作依旧会存在,但是以不可感的方式存在;也并非说现代艺术的作品存在始终不可感,真正不可感的只是作品的“起源”之处,由于技术所内含的转化机制,原作最终会以可感方式呈现自身。然而,当现代艺术最终以可感方式呈现自身时,其存在方式却因技术的介入而带来根本性变化:理念与艺术存在之直接关联性的丧失,使“起源”得以可能的理念由此无法呈现于最终以可感方式存在的艺术作品中。在这一意义上,本雅明将现代艺术的特征概括为光晕的消失,只是这一艺术所显示出来的表征。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真正的差异在于,由于非感性环节的加入,艺术作品与理念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此导致光晕无法直接呈现于艺术作品中。在现代艺术中,光晕之所以不复存在,其缘由正在于此。
二、“永久性”与“暂时性”:艺术存在的思想转换
通过对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对照分析,本雅明以“原真性”和“可技术复制性”分别标识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特质,意图强调的并非原作与复制品的简单分立。单从作品本身来讲,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原作与复制品都是其构成要素,产生不同的关键是对原作的身份认定。光晕未能呈现于现代的艺术作品中,源于“原作”存在方式的变化。由此带来的新问题则是,为何在两种不同的艺术存在中原作的身份发生了反差较大的变化?人们通常从现实环节将这一变化归结为技术的引入,正是借助于技术,作品存在方式的变化才得以实现。然而,如果技术的产生离不开发明技术的人,那么前者改变的只是具体操作环节,造成这一变化的深层依据则在于思想背景的转换。本雅明将艺术的内在特质区分为传统与现代,意图揭示的便是内含于其中的思想背景。
在以“原真性”为核心特征的传统艺术中,原作能拥有光晕,既不是因为原作在被创作时间上相对于复制品的在先性;也不在于原作是由作者所创作,从而拥有由当下性而来的独一无二性。对原作的如此解释源自经验性视角,而当艺术存在被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存在时,则表明这一存在首先关联的是传统思想,呈现出后者的内在特质。在这一意义上,本雅明指出了与传统艺术的“独一无二性”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特点——“永久性”。在传统的思想世界中,艺术能以保持原真性的方式呈现自身的独一无二性,固然是因为其内含光晕,然而光晕能持存于艺术作品中,成为其内在特质,则源于艺术作品对永久性的诉求。正是通过这一诉求,带出了内含在传统思想中的特殊呈现视角——理性视角。现实存在的当下性呈现总是在流变之中,不可能成为永恒的存在。只有从理性角度来审视,现实存在才能迎着这一目光摆脱自身的易逝性,获得与神圣性的直接关联。然而,如果当下性与神圣性呈现为彼此的外在性关系,那么神圣性并不能获得呈现自身所需要的感性存在,当下性也依旧无从呈现自身的独一无二性。由此而言,本雅明强调“独一无二性(Einmaligkeit)和永久性(Dauer)紧密交叉”,与其说是强调艺术作品中“即时即地”的当下性与以传统形式呈现的“理念”一同现身,不如说是意图彰显传统思想中的理性视角对于艺术存在的重要意义。正是借助这一视角,当下性不再是纯粹的当下性,而是由理性来规定,并成为拥有理性规定的当下性。经由这一过程,不但改变了当下性与神圣性的彼此外在性,使其呈现为直接性关系,而且让艺术作品拥有了自身的独一无二性。
古代思想区分“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让理念通过思维规定获得自身的纯粹性,力图彰显的便是这一理性视角。近代思想即使需要以与当下性有关的现实化方式呈现精神性的内涵,也是以扬弃方式对待这一外在于自身的感性现实,剥离其中的不可规定性因素,接纳能够被理性规定并呈现这一规定的感性存在。落实于艺术存在,对永久性的追求是这一理性视角在作品中的呈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强调模仿对于艺术制作的重要性,是因为正是通过这一方式,以“实体”来规范自身的艺术存在得以呈现。黑格尔在《美学》中申明“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也是因为理念通过精神而成就了艺术的审美(感性)存在。在写作《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时,本雅明赋予拥有这一思想内涵的传统艺术以“膜拜价值”,意图强化的是原真性艺术作品中神圣性起源的深层意旨,当艺术成为永恒性的存在时,其已不复是现实的感性存在。在这一总体背景下,传统的艺术存在并不需要通过当下性来获得对自身的展示,光晕能出现于作品中,说明与艺术存在相关的所有内涵均已呈现于此,所需要做的只是借助于艺术的路径通向这一光晕,而“膜拜”表达的便是艺术作品在接近并通向光晕时所引发的客观效应。
对现代艺术而言,本雅明特意将作品存在的内在品性与“可技术复制性”相关联,并不在于凭借日新月异的技术化手段,作品的可复制性相对于传统方式大大提高这一现实状况,而是为着探索通过技术环节来呈现艺术作品所带来的存在方式的变化。在这一意义上,借助与传统相对照而将现代艺术的特征归结为光晕的消失,从而内含在光晕中的神圣性因素无处现身,只是对这一现象的否定性解说。如果现代艺术拥有自身存在的独立品质,就必定内含这一艺术由以立身的思想特质,正是后者构成了现代艺术存在的深层背景。基于这一考量,本雅明指出了与现代艺术之可复制性相关联的另一个特点——“暂时性”。相对于永久性的超越时间性的特征,暂时性首先将艺术存在呈现于时间的流程中,并由此构成与永久性的鲜明对峙。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永久性的消失给艺术作品带来的是消极后果,其古典的魅力不复存在;从现代性角度切入,正是通过暂时性,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显示出不同特点。为了获得永久性,当下性在呈现与神圣性的直接关联时,排除的是当下性自身的现实性,以便理性能够规定自身。与此相比较,艺术作品对暂时性的呈现虽转向永久性的另一面,却非直接与神圣性相对立。在对暂时性的诉求中,剥离的其实是神圣性与当下性的直接关联,并在暂时性对感性存在的呈现中彰显出当下性落实于“此”的现实性。换言之,强调“暂时性(Flüchtigkeit)和可重复性(Wiederholbarkeit)在那些复制品中紧密交叉”,力图显示的是艺术存在中的感性视角。理性视角呈现的是神圣性与当下性的直接关联,并由此而规定出作品的独一无二性;感性视角凸显的则是当下存在的独立性诉求,并在对理性规定的摆脱中呈现出作品存在的可复制性。在现代的思想世界中,艺术之所以不再以原真性的方式呈现自身,并非是因为艺术所内含的光晕离开了作品本身,而是思想由对永久性的追求转向了对暂时性的关注。其所导致的结果是,指向永久性的光晕无法在当下性中呈现。如果当下性是独立意义上的当下性,那么“光晕”的神圣性从根本上外在于这一存在方式。技术方式成为作品存在的内在要素,呈现的恰恰是思想的这一转换。
如果说传统思想的主导思路是由理性来规定感性,因而感性是理性视角下的感性,那么现代思想的努力方向则是以感性的当下为出发点来呈现意义的现实性。尼采以“上帝死了”的方式来凸显“强力意志”对于生命存在的重要意义时,其呈现的是一种由感性立场来面对世界的勇气,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完成对“此”的生存论建构时,则意在阐明由“此在”出发去领会存在的现象学路径。将现代思想的这一诉求落实于艺术存在,对于暂时性的接纳就成为这一现代性方向的艺术化呈现。康德通过反思性判断力的阐明,以鉴赏判断的“单称性”来展示普遍性依据,是在主体视野下的感性呈现方式,而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则通过诗意的栖居来彰显通向真理的艺术路径。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赋予呈现这一思想内涵的现代艺术以“展示价值”,在与“膜拜价值”的对照中凸显的正是现代艺术作品的这一现实化诉求。艺术成为时间性的存在,首先意味着“光晕”的消退,永恒性的不复现身。在这一意义上,虽然艺术的本质都是呈现,原真性艺术的呈现实质上指向的是“膜拜”,因为需要呈现的东西原本就在,而在可复制性艺术中,只有在当下的呈现过程中,艺术存在才得以将自身“展示”出来。
从原真性与可技术复制性的比较,到永久性与暂时性的对照,本雅明不仅阐明了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不同特征,而且揭示出引发这一不同的思想背景的差异。不过,理论分析的目的并不只是对两种不同的艺术存在作出区分,以便把握各自不同的特质;也并非为了从传统艺术的角度出发,以“光晕”是否现身来对现代艺术的存在方式做出评价。纵观《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本雅明对待两种艺术的态度或许内含某种程度的“暧昧”与“纠结”,因为他既“看到了可技术复制艺术的积极意义,却又在文化精英的立场上无限惋惜”。但是,站在20世纪30年代的立场审视,对于传统思想之神圣性的留恋并未掩盖其对于现代艺术之本质的客观解说。如果说分析传统艺术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代艺术,那么这固然在于本雅明对于现代艺术的敏锐把捉,更源于其在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转换过程中对于现代思想背景的深层认可。仅就艺术作品而言,尚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一旦涉及思想的呈现,就不单纯是两个不同路径的对照,由传统到现代,同时展示的是思想本身不可逆转的推进过程。
推进之源内含于近代思想潜移默化的转换中。由主体的视角审视,感性因素虽被纳入其中,成为近代思想的内在要素,却呈现为两条方向截然不同的路径:要么感性依旧以被同化的方式成为理性的规定物,要么感性以呈现自身本色的途径彰显其与理性的内在张力。前者是对传统思想的追慕,后者则是现代精神的萌芽。因而,当感性在现代思想世界中成为基础的出发点后,由感性通向理性之路必然断裂。本雅明的理论探索面对的正是处于转换期的思想背景,他依从了这一思想推进,并从多重角度来体现这一思想转换。在1925年的《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本雅明将关注核心置于17世纪德意志的悲剧作品,通过分析巴洛克时代艺术的“寄喻(Allegorie)”特征,阐明了“悲苦剧”所内含的“形象化本质与其意指之间的深渊”。而在1936年的《讲故事的人》中,本雅明借助对从故事到新闻报道的转化过程的历史描述,揭示了传统故事背后的“经验”因素伴随这一转化而来的逐渐贫乏的过程,如果说故事“一直保留着自己凝聚的力量,即便漫长的时间过后仍能放出异彩”,新闻报道的生命力则“体现在它尚是新闻的那一刻”。至《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本雅明选择的是现代艺术的切入路径,提出的是一个特别的概念——可技术复制性,意图通过永久性与暂时性的对峙而彰显现代思想的深层转换:一旦接纳的是新的思维方式,以感性的视角面对现代艺术,光晕的消失通向的其实是艺术存在与神圣性之间的另一重关系。
三、艺术何以成为媒介?——悖论中的现代性
由艺术存在方式的对照到不同思想背景的比较,不仅呈现了艺术作品各自不同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揭示出走出传统、进入现代的契机。在这一意义上,对“永久性”与“暂时性”所呈现的深层差异的解说,彰显的其实是由理性视角向感性视角的转换。顺着新的视角切入,认为现代思想在对感性存在之独立性的关注中造成当下性与神圣性之间的直接关系不复存在,其实是从消极意义上理解思想背景转换的意义。若从积极意义上审视这一转换,现代艺术存在方式的特殊之处仍需要进一步分析。
就其本质而言,无论以何种方式现身,光晕都是艺术作品呈现自身不可缺少的前提。没有了神圣性因素,纯粹的当下根本无从存在。在这一意义上,强调以光晕的消失作为现代艺术的特质,其实是以传统的视角来看待现代艺术。依从理性的角度,光晕之所以不复存在,是因为光晕所指向的神圣性与永恒性无法通过外在于自身的感性方式呈现。一旦处于现代思想背景中,立根于当下性视角,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张力指向的则是光晕与作品存在之间的间接关系。承载着传统的光晕固然依旧构成艺术作品的深层背景,身处于当下状态的艺术存在却无法直接呈现这一光晕。从艺术存在进入思想层面,光晕与现代艺术之间的间接关系,彰显的其实是当下性存在与永恒性理念之间的彼此异在性。如果艺术作品中的感性存在须经过理性的规定才能呈现自身的独一无二性,那么这一由理性规定的艺术作品并不能呈现真正意义上的感性,借助于技术环节,现代艺术切断了理性与艺术存在的关联性,也因此彰显其神圣性与当下性本质上的外在性。顺着这一思路,现代艺术不再只是我们直面神圣性的作品存在,它通过技术而变身成为我们与异在世界进行沟通的媒介,并由此呈现出自身的“媒介性”。从词源学角度,人们对Media(媒介、媒体)的关注甚早,16世纪末这一术语就已被频繁使用,17世纪初开始“具有‘中介机构’或‘中间物’的意涵”,但是直到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从新的角度重新解说媒介,这一术语的真正意义方才呈现。在1964年问世的专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麦克卢汉首先从人身体的角度切入,认为“一切媒介均是感官的延伸”。这一界定之所以产生重要影响,并不在于它对媒介范围的扩展,使得媒介不再局限于报纸、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等重要媒体,还波及我们生活世界的事事物物;而在于通过将媒介与一般意义上的存在相关联,呈现出处于当代思想背景下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事实:一切以媒介身份存在的事物,都是以感性的方式呈现自身。无论这一媒介是作为身体个别器官的延伸的普通媒介,还是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的电子媒介,均未能改变其落实于当下的感性本质。从本质上讲,要将信息传递给当下世界中的存在,就意味着媒介须以当下世界的方式呈现自身。为了实现这一要求,媒介须得与身体的感性存在相关联。
从这一角度出发,麦克卢汉的另一立论——“媒介即讯息”显示出重要意义。如果说感官的延伸指向的是以当下性为指向的感性存在一方,那么,“讯息”关注的则是其所关联的内容一方,一个外在于当下世界的存在。人们通常认为,媒介的重要性在于其所承载的“讯息”,也尝试创造各种不同的媒介以方便我们获得“讯息”,麦克卢汉却指出,真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影响的并非其所传递的内容,而是媒介自身。这一立论之所以彼时之人难以接受,是因为人们通常从手段意义上来理解媒介,一旦我们面对的不是工具意义上的媒介,而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媒介,那么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讯息”,强调对媒介自身的关注,透露的则是:虽然媒介与其内容相关,但身处于当下世界中的人却无法通过媒介获得这一内容。显然,从词源学上将medium(媒介)与其拉丁文medium相关联,指向“中间”,并非任何一个处于中间环节的事物都可以充当媒介。只有当其所要关联的意义处于我们所无法直面的世界时,媒介才真正显示出自身的必要性。从媒介的产生过程亦可看出,无论是文字媒介,还是技术媒介,其主要目的都是以不同方式完成跨越时空的关联,而这恰恰证明了其所传递之物相对于当下而言的异在性。
由此,在作为一般存在的意义上,媒介通过“中介”首先将自身呈现为一种“转换”。我们的生活世界之所以需要媒介,是因为媒介所指向的信息从根本上外在于当下世界,处于当下世界中的我们无从获得对其之直接感受,而媒介的特殊之处即在于能够将之以我们当下世界中的方式呈现。换言之,媒介通过“转换”关联的信息处于异在的世界,媒介因素呈现的是一个我们无从感知的世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媒介成为现代社会之重要概念的基本条件。虽然媒介能够作为媒介而存在,离不开其所依存的技术条件,只有在当下世界和我们所要关联的世界呈现为绝对的异在关系,作为感官之延伸的媒介才真正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当通过媒介尝试进入我们所无法亲临的世界时,媒介也以信息转换的方式彰显这一世界的根本异在性:我们所能够把握到的充其量只是我们当下的真实感受,而非异在世界的原本状态。在这一意义上,传统世界中的存在物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媒介,在这一世界中,我们虽然也通过各种存在物获得与世界的关联,但信息就在这一世界之中。换言之,媒介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并不在于媒介通过技术手段的更新所产生的传播的便利性,而在于媒介自身的现代性本色。
在面对“媒介”时,20世纪60年代的麦克卢汉是通过对现代世界中一般事物的分析而获得媒介存在的媒介性。回溯至同一世纪30年代,本雅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关注重心是现代艺术,呈现的是作品本身的媒介性。通过技术转换过程,在让光晕无法呈现自身时,现代世界中艺术作品所关联的本质上也是异质世界的存在,也是通过转换方式而为当下的我们所了解。一如通过文字作品,我们获知所未能亲临现场的事件;通过电子设备,我们与无法谋面的他者交流。除此之外,艺术存在另有其特殊指向,它以自身的方式呈现这一媒介性。因为艺术不只是一种媒介,它还拥有其作为作品存在的自足性。这意味着,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在于其并非任何信息的传递者,它们与之发生关联的是传统,是神圣性的存在,然而却是以彼此异在的方式与这一世界相关联。在一般的媒介物中,与媒介相关联的是当下的存在无法直接指向的具体事物,而在艺术存在中,与媒介相关联的是以整体方式存在的传统以及承载着传统的光晕。只不过在传统世界中,直接呈现光晕的传统艺术并不具有媒介性,媒介性只呈现在艺术存在与光晕彼此异在的现代艺术中。在这一意义上,恰恰是通过艺术,媒介的内在本质得以呈现:所要呈现之世界的全然异在性。人们也许会将无法与外部世界产生关联的缘由归结为时空距离的限制,然而真正切断这一关联的缘由其实是彼此的异在性。我们固然可借助科技的进步来消除时空的限制,却无法消除彼此之间深层的异在性,以及由异在性而带来的间接性。而且恰恰是通过时空距离的消除,本质上的异在性才得以凸显。当现代艺术的作品存在意图通过当下性来呈现异在的世界时,正是借助技术的转化方式,媒介性才真正彰显出自身的重要性,并成为现代性的内在特质。
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说光晕的消失成为现代艺术的标志,那么本雅明这一立论的意图并不是要说现代艺术呈现的是碎片化的世界。对于思想的世界而言,呈现神圣性的光晕虽可以销声匿迹,却并非全然不在,曾经出现于历史中的存在依旧会伴随我们的当下生活。在这一意义上,艺术从未曾真正面对全无意义的碎片化存在。以“可技术复制”的方式呈现艺术,固然让原作无从现身,却也依旧提示着原作的不可或缺性。以“媒介”的身份呈现自身,表达的是艺术与光晕之间的另一层关联:艺术以无从呈现光晕的方式关联着这一神圣性。这表明,媒介性呈现的其实是现代思想在其转换中的一个本质性悖论:媒介的存在意味着思想的异在性,意味着我们无法直接通达与直观神圣的世界,意味着我们根深蒂固地依赖于媒介,然而媒介性也同时表明无论如何改善媒介的存在,我们都无从进入永恒世界,还原思想的本真状态。
西方思想的现代转换无疑让艺术的存在拥有了自身的媒介性,由此而言,一种深层的悖论性也成为现代艺术的内在特征,即艺术想要去呈现的精神根本上外在于艺术,并使其由此区分于传统艺术。从根本上讲,媒介内含着现代性的思想根基,并让现代艺术呈现出自身的媒介性。在这一过程中,以“可技术复制”的方式呈现艺术,只是由技术层面的改进所带来的艺术制作方式的变化,艺术由这一技术方式而指向的媒介性才真正成为现代艺术彰显其悖论性的内在路径,并成就了本雅明作为“一位现代性(modernité)的作家”的本色。
四、从“消遣性接受”到存在的“星丛”:媒介艺术的诠释学向度
如果说通过媒介性,现代艺术显示出深层的悖论性,并由此彰显艺术的现代性本色,那么,注定不可能获得光晕之呈现的艺术又如何呈现自身的存在?正是在面对这一问题时,艺术的媒介性显示出自身的另一层意义。通过作品的媒介身份,现代艺术呈现出自身的悖论性:一方面与拥有神圣性的传统有着无法剥离的关联,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光晕实际上无从获得的状态。然而,如果作为媒介的艺术不只是在呈现光晕,它还同时以“转换”的方式呈现这一光晕,就意味着以间接转换方式存在的艺术凸显的其实是当下存在的重要性。麦克卢汉强调“媒介即讯息”,固然是为了表明这一“讯息”的异在性,更是为了彰显“媒介”自身的重要性。落实到艺术存在同样如此。现代艺术虽不再能让神圣性在场,却依旧可通过自身的方式呈现神圣性。对前者来说,现代艺术指向的是呈现自身的思想背景,它表明,不可能呈现的存在依旧拥有其对抗碎片化存在的意义;就后者而言,现代艺术彰显的则是呈现自身的现实使命,它宣称,即使是以自身的方式,也依旧是指向神圣性的路径。因而,如果神圣性注定无从现身,那么首先应当做的工作就是搭建起通向神圣性的路径;如果已成为异在的光晕注定销声匿迹,那么作为转换过程的媒介必定成为实际的关注重心。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由传统到现代的另一层诉求得到彰显。以与传统相对照的方式来面对现代艺术,确乎能够呈现现代艺术的不同特点,但现代艺术依旧是处于传统背景下的艺术,要想使其成为真正的现代艺术还需要真正置身于现代的思想背景,以现代性的视角来面对艺术存在。之所以直面的是现代艺术的悖论性存在,是因为我们虽已通过艺术呈现感性自身的当下性,而非由理性所规定的感性,因而在根本上外在于神圣性,但是理性所依托的传统背景依旧被认为是艺术存在的结构要素。产生悖论的深层缘由正在于两个因素之间由彼此异在而产生的张力。一旦真正以现代性的视角来面对当下性,那么悖论性存在便由焦点转化为背景,因为神圣性的光晕虽无以呈现,却不意味着当下的存在不会拥有与自身相契合的“光晕”。不可否认,艺术存在的现代性悖论推进了这一转化过程,也让感性存在自身的深层意义得以彰显。当本雅明以积极态度面对现代艺术,尝试发掘其潜在可能性时,就表明这位徘徊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学者已完成现代性转换,并以艺术方式开始现代性的思想建构,即不是在与传统相对照的意义上面对现代性,而是以当下存在自身来呈现现代性。
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现代性视角的呈现集中体现为对“消遣性接受(Die Rezeption in der Zerstreuung)”的分析,其目的是彰显当下性存在的独立性。一旦思想的现代转换将关注视角落实于感性存在,当下存在由此获得其在这一思想背景下的中心位置,首先随之而呈现的则是与这一当下性相关联的生存感受。因而,本雅明着重强调“消遣性接受”是“随着日益在所有艺术领域中得到推重而引人注目,而且它成了知觉已发生深刻变化的迹象”,这并不意味着通过它来呈现大众在面对艺术作品时的一种主体感受,而是艺术作为一种当下存在方式的生存论展示。从传统的思想背景来审视,消遣性接受采用“熟悉闲散的方式”,呈现的似乎是略显消极的状态,因而也常常被认为具有大众文化的特性。从现代思想的角度切入,无须聚精会神的状态并不意味着纯粹的放松,而是为着由此彰显现代艺术的感性特质。传统艺术之所以强调“凝视专注”,在于这一感受的重心是要通过联想方式进入沉思状态。传统艺术呈现的“膜拜价值”关注的是艺术的神圣性,指向以永久性为特征的“光晕”,而正是通过这一沉思状态,感性存在方能获得与神圣性的关联。与此相对照,“消遣性接受”以闲散的方式进行,则是将真正的感性状态归属于现代艺术。如果说现代艺术的“展示价值”聚焦于艺术自身存在的当下性,关注的是通向已经无从现身的光晕的过程,那么熟悉闲散的方式凸显的正是这一处于自身状态的感性特质。
因而,在对“消遣性接受”作进一步解说时,本雅明特别指出其与触觉的关联性,因为“触觉方面的接受不是以聚精会神的方式发生,而是以熟悉闲散的方式发生”。这倒不是说,我们只是通过触觉来面对艺术世界,恰恰相反,在对电影的影像感受中,更多运用的其实是视觉能力,获得的却是如同触觉一样的生命触动,因为触觉作为可触性感觉本质上通向的是生命的感受。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对各种感觉进行分析时就曾指出可触性感觉的一个重要特点:与生命存在的本质关联,没有触觉的生命无从存在,并由此强调了触觉作为一种感觉对于感性存在的重要性。近代美学从词源学上将趣味概念与味觉相关联,亦非只是表明趣味是由味觉这一感官感觉引申而来,而是强调味觉作为可触性感觉所通向的生命感受对于趣味能力的至关重要性。本雅明凸显触觉在当代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无疑也与这一感受的本质特点有关。因而,通过将“消遣性接受”与触觉相关,这一概念的本质性内涵得以呈现:强调触觉与生命感受的关联,意味着消遣性接受呈现的并不是传统的被动意义上的感性,而是一种主动呈现意义上的感受。
就这一点而言,电影艺术所带来的“惊颤效果(Schockwirkung)”可作为典型代表。如果说“消遣性接受”成为现代艺术的一种主导性接受模式,那么这一接受模式之核心内涵便是“惊颤体验(Chockerlebnis)”。在1939年的《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中,本雅明以对波德莱尔的诗的分析为切入点,展开说明了现代艺术的这一本质特征,并认为在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艺术中,“惊颤作为感知的形式已被确立为一种正式的原则”。因为当电影中的画面纷至沓来时,现身于其中的观赏者获得的与其说是一种生活的体悟,不如说是一种生命的感受。如果说前者让我们发现了诸种感受中的思想魅力,后者集中呈现的则是生命的律动。在传统的意义上,人们常常期待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可以获得生命感受的升华,因为恰恰是在这一升华中内含着普遍性的诉求和理性的思考。但在现代艺术看来,生命的感受同样也可以拥有自身的意义,“惊颤体验”彰显的便是属于感性自身的意义。
于是,正是在对以“惊颤体验”为特征的当下存在的呈现中,本雅明将现代艺术的本质与“可技术复制性”相关联就显示出深层意义:“可技术复制性”并非只是由于技术的引入而赋予现代艺术的一个表征,而是同时成为这一艺术重新获得自身之“光晕”的内在诉求。如果说现代艺术在根本上处于时间的流程之中,呈现的是暂时性的特征,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彻底放弃了神圣性,成为纯粹碎片化的存在。对神圣性的呈现和这一呈现实际上不可能的张力,揭示的是现代艺术的潜在方向。虽然神圣性无从现身,但通向神圣性的过程并非全无意义。因为未能通向纯粹的神圣性,却由此展示出处于时间流程中的神圣性,即一种属于感性的神圣性。
问题是,如何呈现这一感性的神圣性?为解决这一问题,现代艺术关注可复制性的真正用意彰显。凭借技术方式获得可复制性,固然是为了满足量化需求,“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更重要之处则在于通过它“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于是,通过可复制性,处于时间流程中的艺术获得另一种超越时间的方式,即在时间中超越时间的方式。正如唐宏峰所说,从根本上讲,“复制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而非复制技术从古至今不断演进的历史连续发展的问题”。换言之,“可复制性”只有在现代艺术中才呈现出自身本质上的重要性。在传统艺术中,原作与复制品的分立,内含的是艺术存在与其“可复制性”的外在关系;对于现代艺术而言,原作与复制品的重合性并非只是因为技术的介入,而是为了表明现代性艺术存在中作品与其“可复制性”的内在关联。本雅明强调“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意在指出,并非复制品在现代艺术中获得了不同于原作的独立身份,而是“可复制性”成为现代艺术的内在特征。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现代艺术通过作为媒介的原作呈现出自身的当下性,那么可复制性作为内在要求彰显的则是艺术自身的诠释学向度。
1960年,当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出版了使其一举成名的著作《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在这部哲学诠释学的开山之作中,伽达默尔通过区分作为方法的诠释学,提出一种呈现真理的诠释学,从而将对理解之可能的解说上升为人的本质性存在方式。从对核心术语“诠释学”(Hermeneutik)的词源学梳理可看出,在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之间,信使赫尔墨斯具有特殊意义。之所以需要信使,是因为神的世界从根本上外在于人的世界,需要通过信使传递神世的信息,而当赫尔墨斯以人的语言来传递这一信息时,一种意义的转化已内含其中,这意味着人所能接收的只是以人世形式呈现的信息,而非神世的信息。于是,信使作为一种转换信息的媒介也内含自身的悖论性。将术语的词源学含义落实于人的实际生存状态,伽达默尔经由“观赏者”的特殊视角阐明了“此在”作为在世之在的一种“同在”结构。通过将“游戏”作为一种存在论事件引入在世,伽达默尔认为,能够让游戏呈现于此的并非游戏者,而是观赏者。在以“游戏者”的方式呈现游戏之时,因为二者之间的直接性关系,游戏者通过对规则的遵守带来的反而是自身存在的消弭,它被同一于游戏活动。与此相对照,“观赏者”的身份满足了“同在”所具有的“外在于自身存在(Aussersichsein)的性质”,从“观赏”的角度来呈现游戏存在且恰恰因为这一悖论性的存在,游戏才真正得以同在“此”。
将诠释学由对真理的呈现而引入艺术存在,“同在”作为一种对“此”的生存论建构无疑与本雅明对现代艺术的分析产生了本质性关联。如果说艺术媒介的悖论性存在是“同在”这一在世之在的艺术化呈现,解释学视野下“同在”的生存论建构其实是对艺术之媒介性的哲学解读,二者共同彰显的是现代性的思想背景。由这一思想背景反观,可复制性是对现代艺术的意义彰显。在传统艺术中,原作与复制品是判然有别的存在,复制品只是一种附属性的存在,并不能替代原作的存在方式,而在现代艺术中,原作的媒介身份恰恰使可复制性成为作品呈现自身存在的必要环节。一旦艺术将自身置于现代性思想中,呈现的是自身的“暂时性”,那么正是通过原作的“可复制性”,艺术才能以走出暂时性的方式获得自身的丰盈。通过独立于“原型”的“摹本”,伽达默尔让“此在”呈现出“在的扩充”,而本雅明则通过原作的“可技术复制性”呈现出存在的“星丛”(Konstellation)。
早在1925年的《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本雅明就对理念这一传统概念做了新的解释,认为理念就是“星丛”,而“理念与物的关系就如同星丛与群星之间的关系”。到了写作于1926—1940年的《拱廊街计划》中,本雅明则从艺术存在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影像(Bild)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其中,曾在(Gewesene)与当下(jetzt)瞬间聚合为星丛。换言之:影像是停顿的辩证法(Dialektik im Stillstand)。现在(Gegenwart)与过去(Vergangenheit)的关系是一种纯粹时间的、延续的关系,但曾在与当下的关系却是辩证的:不是过程而是影像,是跳跃的影像(sprunghaft Bilder)”。在这段经典解说中,指出“曾在”与“当下”聚合为“星丛”,揭示的是本雅明思想的诠释学底色——以“同在”为艺术存在的根基;强调影像的呈现不是“过程”而是“跳跃”,彰显的则是艺术通过“可复制性”而来的空间性维度。换言之,将这一存在方式概括为“停顿的辩证法”,表明本雅明有着与伽达默尔相同的诠释学指向,却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如果说伽达默尔是从同在的时间性角度呈现艺术存在的诠释学特质,那么本雅明则是从同在的空间性角度展示艺术存在的诠释学向度。
结语
以“可技术复制性”来标志现代艺术的特征,是因为现代艺术借助于技术的变革而得以呈现自身的本色。然而,这一特征却不是通过原作与复制品的直接对峙而彰显。真正发生变化的首先是以“原作”方式呈现的艺术存在。当传统艺术将内含神圣性的“光晕”直接呈现于艺术形式时,现代艺术则通过技术对于可感性的消除而显示出光晕与艺术作品之间的间接关系。不过,技术带来的变化只是表征,思想背景的转换才是其深层缘由。传统艺术之所以内含光晕,根本上缘于传统思想的理性视角。后者通过对摆脱时间流程的“永久性”的追求而呈现,由此成就了艺术存在与光晕的直接关联。与此相对照,现代艺术之所以不复呈现光晕,则是因为思想在现代性转换中所内含的感性视角,并借助以当下性为基点的“暂时性”而呈现。在这一意义上,“光晕”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神圣性不复存在,而是通过其与艺术存在的间接关系呈现出神圣世界的异在性。正是这一思想背景的变化使得现代艺术显示出本质的媒介性:以转换呈现形式的方式来揭示无法直接显示的异在思想。也通过作为媒介的艺术显示出现代性的深层悖论:现时代的生活世界需要呈现光晕,而当艺术是通过转换形式而存在时,就意味着呈现光晕实际上的不可能。
然而,在现代性的进程中,悖论并非纯然消极的,而是内含积极的努力。在以当下性来呈现光晕的现代艺术结构中,虽然神圣性不可得,当下性的呈现过程亦具有自身的意义。如果说现代艺术的关注重心不再是对思想之永恒性的探寻,而是带着这一诉求进入对感性存在之当下性的呈现,那么正是在这一双重交织中,“可复制性”彰显出自身的根本重要性。这一在传统艺术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外在于原作的存在,在现代艺术中以特殊方式进入原作,并成为现代艺术的内在诉求:通过原作中所内含的“可复制性”,当下性的存在获得了超越当下性的呈现。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彰显出自身的诠释学维度:不是对注定会结束的精神的历史性展开,而是对当下存在之现实性的“跳跃”式生成。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1期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公众号2025年01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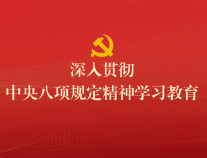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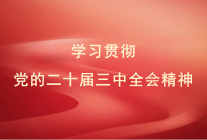



 潘梓年
潘梓年 金岳霖
金岳霖 贺麟
贺麟 杜任之
杜任之 容肇祖
容肇祖 沈有鼎
沈有鼎 巫白慧
巫白慧 杨一之
杨一之 徐崇温
徐崇温 陈筠泉
陈筠泉 姚介厚
姚介厚 李景源
李景源 赵汀阳
赵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