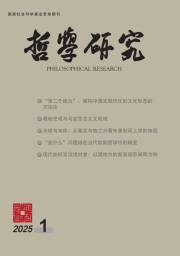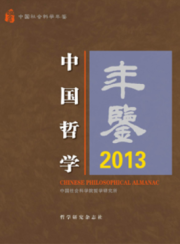【王齐】用或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
摘要:克尔凯郭尔其人其思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已有百余年历史。近五年来,随着十卷本《克尔凯郭尔文集》以及两部国际克尔凯郭尔研究界重量级《克尔凯郭尔传》的中译本相继出版,对克尔凯郭尔的阅读和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势在必行。鉴于克尔凯郭尔的非学院派写作是一场生命与作品交织的过程,离开了对其生活故事的了解,尤其是离开了对其包含假名、反讽、隐喻等特征在内的“间接沟通”写作方式的把握,读者很可能会错失克尔凯郭尔作品所欲传达的思想主旨,因此首要的阅读方式是以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以期达到对其作品的同情式理解。作为事情的另一面,“间接沟通”的写作方式为直接理解克尔凯郭尔思想设置了重重障碍,同时也使克尔凯郭尔文本呈现复调特征,因此,还需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在同情式理解和整体性理解文本的前提下,努力捕捉那些溢出克尔凯郭尔原初写作意图的东西,最大限度地令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当代化。
关键词:克尔凯郭尔;间接沟通;复调性;当代化
一、引子:反思克尔凯郭尔研究的契机
鲁迅1908年在《文化偏至论》中首次引进“丹麦哲人契开迦尔(S.Kierkegaard)”,此后克尔凯郭尔其人其思在文学艺术界一直拥有热爱者,在学术研究界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近年来克尔凯郭尔研究界发生了两件大事,在某种意义上改写了中国的克尔凯郭尔接受史:一件事是2020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合作的十卷本《克尔凯郭尔文集》全部出版完成。这套“蓝皮书”系汉语学界首次系统引进最新丹麦文学术版《克尔凯郭尔全集》(Sren Kierkegaaards Skrifter),且直接从丹麦文进行翻译,译本带有大量研究型注释,为克尔凯郭尔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性文本,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初市面流传的从《非此即彼》和《人生道路诸阶段》中撷取翻译出版的《勾引家日记》和《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的“黑历史”永远成为过去,克尔凯郭尔研究与对西方哲学史上其他人物的研究具有同等的学术和思想价值。另一件大事包括了两个部分,分别发生于2019年和2024年,两部国际克尔凯郭尔研究界重量级《克尔凯郭尔传》的中译本相继出版:周一云翻译了丹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现任主任、作家尤金姆·加尔夫(Joakim Garff)于2000年用丹麦文出版的传记,南开大学哲学院刘子桢翻译了奥斯陆大学荣休教授、国际知名克尔凯郭尔研究学者阿拉斯泰尔·汉内(Alastair Hannay)于2001年用英文出版的传记。两部传记集中反映了国际范围内自20世纪70年代因后现代主义兴起而复兴的克尔凯郭尔研究的前沿成果,前一部生动流畅,后一部视野开阔,中文读者终于可以彻底摆脱克尔凯郭尔早期英译者沃尔特·劳瑞(Walter Lowrie)于1942年出版的那部带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传记了。
两件大事的出现标志着中文克尔凯郭尔研究步入正轨,当此之时,有必要严肃反思阅读和研究克尔凯郭尔的方法。克尔凯郭尔是非学院派哲学家,虽然在经过了20世纪存在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发现之后,如今的我们不必再论证克尔凯郭尔作为哲学家的合法性,但对于受理性主义线索统摄的西方哲学训练的人来说,如何阅读和把握克尔凯郭尔以“间接沟通”的写作方式所完成的文本仍然是一个问题。我愿意提出两种不同的阅读克尔凯郭尔的方式——用或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并以例证的方式讨论两种阅读方式的得失。
二、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
提出这个命题是因为克尔凯郭尔的写作本身就是一场生命与作品交织的过程,离开了对其生活故事的了解,尤其是离开了对其包含假名、反讽、隐喻等在内的“间接沟通”写作方式的把握,读者很可能会错失克尔凯郭尔作品所欲传达的思想主旨,至少很难达到对他的作品的同情式理解,甚至极有可能落入他的反讽策略所设下的圈套。
(一)传记之于克尔凯郭尔研究的意义
哲学是普遍之学,一般而言,当阅读一部哲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并不必须了解创造这种哲学的人的生活故事,在这个方面,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的话常常被引用:“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如果说黑格尔此言完美体现了其思辨哲学的立场,那么,当克尔凯郭尔把自己的首部假名作品《非此即彼》的副标题定为“生活片断”(Et Livs Fragment)的时候,当他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地说自己的全部作品是献给父亲和未婚妻瑞吉娜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从他的作品中读出他与瑞吉娜的“暗码通信”的时候,黑格尔这句话的不恰切性就开始显现出来。再进一步,如果我们认同海德格尔的立场,即哲学起源于实际生活经验然后又会跳回到实际生活经验之中,那么哲学家的生活经验与其哲学思想之间就会存在一种创造性张力,至少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情况是这样的。因此,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是我们走入其作品和精神世界的途径,而传记阅读又是这个路径的方便法门。
(二)后现代语境下的克尔凯郭尔传
克尔凯郭尔是“富贵闲人”,是哥本哈根市民眼中的“怪人”,是1877年为克尔凯郭尔写下首部传记的丹麦文化史家、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眼中的“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深刻的心理学家之一”,是劳瑞牧师眼中的“基督教的殉道士”。或许因为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虽然身为丹麦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头像却缺席哥本哈根大学广场。作为克尔凯郭尔的哥本哈根同乡,尤金姆·加尔夫显然注意到了这个尴尬局面。加尔夫在他所创作的传记“引言”中指出:“在对克尔凯郭尔的典型介绍中,人们无疑乐于居高临下地将作为个人的克尔凯郭尔当作天才著述后面的一段古怪附录。”或许这就是加尔夫为克尔凯郭尔立传的动机。
加尔夫写作克尔凯郭尔传拥有两大天然优势:一是他非常熟悉克尔凯郭尔的全部发表作品,作为母语阅读者和出色的丹麦语写作者,加尔夫对克尔凯郭尔的写作风格和语言特色的把握无人能敌。二是加尔夫是最新学术版《克尔凯郭尔全集》的编者之一,这使他在第一时间有机会接触根据克尔凯郭尔手稿重新整理、编辑的大量“日记-Journalerne”;同时还有机会参照克尔凯郭尔的书信以及哥哥彼得的日记、信件等原始材料。如果用一句话对这本600多页的厚书的优点进行概括,那就是加尔夫透彻理解了克尔凯郭尔“日记-Journalerne”的性质。这些“日记-Journalerne”并不是打开克尔凯郭尔心灵之窗的钥匙,仿佛这些重新整理的日记能够解答其假名作品当中的谜团;它们只是克尔凯郭尔的另类“作品”,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虚构的故事,因为“自由的虚构化写作”是克尔凯郭尔喜爱的形式。如是理解当与克尔凯郭尔“间接沟通”的写作策略是一致的,克尔凯郭尔就像狡黠的猎物,小心地不让猎人发现自己的踪迹。在这个原则之下加尔夫指出,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过去”不是“记忆-husker”,而是“回忆-erindrer”,因此概念虚构与实际事件几乎无法分开。以克尔凯郭尔笔下的父亲形象为例,加尔夫发现,这位父亲“忽而以无上的权威出现,足以让旧约式的父权秩序相形见绌,忽而又呈现为几乎超凡入圣的幻象,让全世界的童话显得像是凄惨的散文,让最美的林地枯萎”。但老克尔凯郭尔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并不知道,虽然克尔凯郭尔在发表的作品和日记中写得太多。
有了上述前提作为基础,加尔夫采用“尊重事实”的态度和“小说技法”,努力重建克尔凯郭尔从中成长起来的生活与写作之间的活跃对话,希望最终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全面意义上复杂的克尔凯郭尔”。通读过这本传记的人可以说加尔夫的心愿实现了。伴随着对克尔凯郭尔走过的大街小巷、对其看书时折书角的习惯的描写,对包括菜单、酒单、裁缝账单等在内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尤其是对克尔凯郭尔所由之成长和生活其间的丹麦文化和艺术复兴的“黄金时代”的全景图的勾勒,克尔凯郭尔的形象鲜活了、立体了,我们有机会清楚地看到其生活与作品之间的张力。加尔夫肯定是怀着爱才写作这部传记的,但他不是为了赞美,甚至不是为了揭秘、解谜,而是为了真实复现一个复杂且有着深度思维能力的克尔凯郭尔。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说他的家人活不过34岁,他直言那是因为耶稣受难是在33岁。这是把克尔凯郭尔打造成宗教殉道者的绝佳材料,但根据加尔夫的研究,这个念头其实只是父子俩在“深沉的抑郁”中共同培育出来的想法。这个想法欺骗了包括哥哥彼得在内的所有读者,而克尔凯郭尔早年为自己评论安徒生小说《不过是个提琴手》所起的标题《尚存者手记》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效果。克尔凯郭尔在虚实之间自由游走的写作方式表明任何对其“间接沟通”的写作方式置之不理的阅读都会导致理解的错位。
(三)广阔哲学史视野下的克尔凯郭尔传
与加尔夫立传的初衷相似,汉内写作克尔凯郭尔传也是为了展现“一个在多样化话题和风格中展现的、自我教育的个体”。汉内是一位颇有学究气质的克尔凯郭尔研究者,他更关心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理解克尔凯郭尔。为达此目的,一方面,他指出若不了解克尔凯郭尔与其时代、文化和一般生活的关系,我们将不可能正确地阅读克尔凯郭尔,这一点与本文的第一种读法完美契合。汉内说:“如果认为生活不能告诉我们如何理解文本,那将是荒谬的。这里所讲的故事是一场抗争、一场竞争,甚至是一场战斗,一场由克尔凯郭尔挑起的与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冲突。”另一方面,他又有意识地把克尔凯郭尔的作品放置于更为广阔的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发展线索之下,从哈曼、黑格尔、谢林、罗森克朗兹,到维特根斯坦、卢卡奇,而不仅仅像加尔夫那样侧重于丹麦的“黄金时代”。当汉内不再把克尔凯郭尔视为存在主义的先驱,而是视为“一位对个人,尤其是道德心理学有着深刻见解的作家”的时候,他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例如在解读《忧惧的概念》一书时,汉内在有限的篇幅内概述了“忧惧-Angst”的概念史:从这个概念在浪漫主义作品中的发端,到克尔凯郭尔引用过的哈曼为之赋予的“神圣”的描述,再到作为心理学概念在德国观念论中的应用,比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就对之持有否定态度,因其表现出了意识无法做到内在与外在的真正统一。在汉内看来,《忧惧的概念》不同于黑格尔之处在于黑格尔描述的是历史和集体意识中精神的发展,而克尔凯郭尔描述的是个体意识的发展。在论及《致死的病症》的时候,汉内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既关乎克尔凯郭尔的“肉中刺”,又关乎丹麦社会的疾病。而书中提出的“自我是无限和有限的有意识的综合”中的“综合”,并不具有黑格尔式的“调和”的意义,而是个人需要为之努力的目标。虽然汉内在传记开篇说“传记作者必须重点关注传主的生命(bios),而非著作的经历”,但实际上这本传记更像是汉内本人对克尔凯郭尔作品和思想的整体性解读,涉及克尔凯郭尔生活的内容只是解读文本的一个作用有限的索引。汉内谦逊而严谨的学院派作风使他总想为读者提供对克尔凯郭尔文本全面且权威的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他本人似乎又对不同的立场都有所保留地赞同,原因在于他认为克尔凯郭尔文本自身的丰富性和复调性特点,结果他本人的观点有时显得较为隐蔽,需小心辨析。
有的时候,当汉内的学院派风格遭遇克尔凯郭尔的反讽的时候,也会出现“不兼容”的现象。比如,针对克尔凯郭尔喜爱令“心理学”这个术语出现在著作标题中的现象,汉内为克尔凯郭尔的假名著作贴上了标签,认为《哲学片断》是“一小点、一块碎片、一小粒”哲学,《忧惧的概念》是心理学。不过作为一名治学严谨的学者,汉内很快又自我解构了这种区分,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忧惧的概念》像克尔凯郭尔的许多其他著作一样徒有专著的外表,因其多变的风格和大量使用隐喻等特点而并不容易被定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同一些欧美学者一样,汉内执着地纠结于克尔凯郭尔“Philosophiske Smuler”(《哲学片断》)一书当中smuler一词的译法,并且因为该词有“面包渣”的意思,从而判定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英译本采用的Philosophical Fragments不恰当,希望以Philosophical Crumbs取而代之。问题是,“面包渣”只是smuler的一个意思,这个词自身还有“一点点”的意思,因此选择crumbs颇有以偏概全之嫌。此外,用fragments与smuler对应,能够有效体现出克尔凯郭尔非体系哲学写作的意图,同时还能展现这本书表面的“片断性”与内在的“体系性”之间的巨大反差所制造的反讽效果。
汉内没有像加尔夫那样明确把克尔凯郭尔的“日记-Journalerne”作为他的另类“作品”,也就是说,他没有关注到这类“作品”的虚构性质,这是令人遗憾的。加尔夫对克尔凯郭尔著名的1835年吉勒莱日记有过精辟的分析。他注意到,在日记的前半段,克尔凯郭尔明确提出“我要做什么”的命令优先于“我要知道什么”;他还提出自己要“寻找一种为我而在的真理,寻找一种我将为之生、为之死的观念”。加尔夫高调地指出,从生平研究的角度看,这段宣言就像是奥古斯丁或路德式的“突破性文本”。他敏锐地注意到,这段宣言之后的内容鲜有人引用,这里克尔凯郭尔提出自己有意投身法学,甚至想构建一种小偷的生活,或者有意当一名演员,因此加尔夫果断地将之视为克尔凯郭尔人生的一个“替身”。相比之下,汉内则把神偷的构想解读为克尔凯郭尔为“独狼的角色所吸引”,从而把“一意孤行,单枪匹马”作为克尔凯郭尔复杂写作动机中的一个座右铭。传记作者对传主的生活和作品没有终极解释,只有更合理的解释;加尔夫和汉内的解释哪个更合理,读者自有评判。
加尔夫和汉内都未能抵挡住对传主进行心理分析的诱惑。汉内原本就有探究克尔凯郭尔写作的心理动因的意愿,在讨论《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的时候,汉内首先给出了关于该书一系列的哲学和神学的解读方案,包括这本书是费希特主体性理论的修订甚至是神学改写,以及从康德、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传统向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转向的尝试。之后汉内还提出了克尔凯郭尔写作这本书的狭隘动因,即他“生性爱争辩”,所以他搅在其同时代神学家明斯特、索湖学派和格伦德威之间,为了斗争而斗争。汉内一方面承认前者是因为克尔凯郭尔文本的丰富性,另一方面认为后者的看法非常狭隘,但“不完全是异想天开。至少它探究了克尔凯郭尔写作的心理学动因,而这正是大量文献所做不到的”。汉内总是在关键的冲突上态度游移,有所保留。相比之下,加尔夫的态度和决断要鲜明很多,他没有控制住对克尔凯郭尔进行心理分析,行文中不止一处大胆而直接地论及写作之于克尔凯郭尔的治疗的意义,论及克尔凯郭尔的“涂写癖”。问题是,从成为作家的那一天开始,克尔凯郭尔就在哲学上反对黑格尔“内在与外在相统一”的论调,坚持认为“内在的不同于外在的”;在写作上他亦主动设置重重障碍,不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被他人窥视。因此,对传主进行心理分析的诱惑最好得到控制,最大限度地维护作者生活与作品之间的张力关系。
(四)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的可能误区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只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所可能陷入的误区。其一,这种方式只依赖从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中寻求启示和答案,这不仅是对像克尔凯郭尔这样深谙“思想的无限运动”的思想家的无效制约,而且往往会令我们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比如克尔凯郭尔的“肉中刺”,无论如何搜集材料和进行心理分析,我们都无法确切知晓那究竟是什么。有时我们还会发现克尔凯郭尔的诸假名作者之间有相互解构的可能性,从而使得研究者在刚刚得出结论的同时就不得不自我解构。其二,忽略“间接沟通”会导致英国学者罗吉尔·普尔(Roger Poole)所说的“直白阅读”或者“迟钝阅读”(blunt reading)。普尔认为,克尔凯郭尔的假名作品从根本上是一种“文字神秘”的展现,读者应该像阅读侦探小说那样随着文本所展现的神秘结构和情节“飘荡”,而不要去做任何将其体系化的努力。显然,普尔是在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所说的方法无异于放弃哲学的工作。于是,在提出“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之后,我们需要提出一个相反的命题——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
三、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
提出这个与前述相反的命题,除了这是以哲学的方式从事哲学史研究应有的态度之外,单就克尔凯郭尔“这个个体”而言,命题具有特定的意义。
(一)“反讽”的陷阱
根据前述,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是我们步入这位丹麦“怪人”的作品和精神世界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克尔凯郭尔在用生命写作的同时反讽的态度和立场从未离他左右,通过带有特定涵义的假名作者姓名的设计(如《哲学片断》和《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的作者名为“爬天梯的约翰尼斯-Johannes Climacus”,一个历史上的知名隐士与普通丹麦男子名的结合),通过不经意地在写字台抽屉中发现手稿的情节(《非此即彼》上卷),通过制造文本套文本的“中国盒子”的效应,克尔凯郭尔一直是有意识地与自己的作品拉开距离。这些策略一方面为读者真正走入他的精神世界制造了障碍,另一方面也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毋庸置疑的复调性,为我们的多样性阅读打开了空间。
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首先意味着彻底抛弃对其进行心理分析的念头。不要试图绕到作品背后去挖掘写作背后的“意思”(Mening),这是假名作者在“间接沟通”的策略下一直躲闪着不愿直接给出的。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还意味着在同情式理解和整体性理解克尔凯郭尔文本的前提下,去努力捕捉那些溢出克尔凯郭尔原初写作意图的东西。克尔凯郭尔没有且没有意愿构建自己的概念王国,他基本沿袭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思辨哲学传统的概念体系。他从大学时代就发现了思辨哲学的问题,但他的工作重在批判而非建构,而且他的批判还常常与揶揄和嘲讽混在一起。于是,去发现克尔凯郭尔用非体系的、反讽的方式所从事的反思辨哲学传统的工作,就是哲学研究的任务,也是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的方法的主旨,这项工作可以从向前和向后两个方向进行。
(二)回溯式的影响研究
向前的方向离不开影响研究,这个方向的代表当推约翰·史都华(Jon Stewart)主编、集全球克尔凯郭尔研究力量完成的大型系列著作《克尔凯郭尔研究:原始资料、接受史和参考资料》。这套丛书除了对克尔凯郭尔接受史进行了全球范围内的总结和回顾外——截至2005年对中国大陆克尔凯郭尔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特点的梳理与分析也被收入其中,它的重心更大程度上落在处理克尔凯郭尔与西方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之上,相当于对克尔凯郭尔所受到的影响进行了一次扫荡式的研究,提供了包括《克尔凯郭尔与〈圣经〉》《克尔凯郭尔与神学》《克尔凯郭尔与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以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主义》等多个主题和卷册,几乎提供了一幅截至21世纪初期的克尔凯郭尔研究的全景图。
与此同时,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对克尔凯郭尔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的研究也是这个方向的典范。在《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一书当中,亨利希一反学界只关注克尔凯郭尔与黑格尔的关系的路径,从费希特知识学“消除哲学与生命之间的鸿沟”的要旨出发,独辟蹊径地把克尔凯郭尔置于费希特知识学的理论框架之内,虽然着墨不多,但却为我们理解克尔凯郭尔的理论开启了新的可能性。亨利希指出,费希特扩大了知识的范围,他把所有“包含概念要素的过程”都纳入知识学的范畴。如此,像“冲动”“渴望”“梦想”这些“心灵是其所是的方式”,都成为使人成为自身的规定。在亨利希看来,费希特“知识学”不是把人类的原初经验而是把经过充分发展了的人类经验置于哲学理论之中,从而使得哲学理论以心灵哲学为导向。在这个总的认识之下,亨利希提出克尔凯郭尔紧随费希特,在《致死的疾病》中对由“渴望”定义的心灵类型进行了细微的描述。又因为“渴望”总是对某物的“渴望”,心灵概念必然有对应的相关事物,因此心灵概念需要一个“世界观—世界图像—Weltanschauung”,二者的关联引发了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和《人生道路诸阶段》中展开的“感性”“伦理”和“宗教”的个人发展阶段理论,它们可以作为三种生活方式同时并存。
(三)克尔凯郭尔思想的当代化
回溯式的影响研究有助于理解克尔凯郭尔的精神成长史,但这无助于开启克尔凯郭尔思想中通往未来的面向,这一点无法满足“思想的无限运动”的内在需求。因此,更有力度的方式是向前,令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当代化。
以“跳跃”(Spring/leap)概念为例。汉内曾指出,“跳跃”可能是克尔凯郭尔思想中被理解得最少的概念。他认为在《非此即彼》中,读者能够明确感受到从感性到伦理的方向,但却找不到关于“跳跃”的线索或暗示。如果汉内移步到《哲学片断》和《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他或许可以修正这个看法。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跳跃”概念不是用来描述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转换,而是用来描述神的出场方式。在《哲学片断》中,克尔凯郭尔认为神不会从关于其存在的证明当中出场。相反,只有当我们“松手”即放弃证明的那个瞬间,神的存在才会显现。在《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中克尔凯郭尔更进了一步,指出“跳跃”是逻辑论证过程中缺失的环节。不过他没有像一般的哲学家那样对逻辑论证中的缺环感到羞耻,反而赞誉这种缺失为“思想中的抒情性顶点”。可以说,在克尔凯郭尔眼中,事关信仰的逻辑证明方式是无效的,这里需要的就是轻盈的“跳跃”,那是个体的决断。汉内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跳跃”不是对信仰的“非理性赞同”,它“更像是当理念无法再以思想或理智(thought or reason)的形式拥抱生活时,为继续前进而必须做出的果断选择”。
但是,如果我们只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事情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只有当我们选择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之时,“跳跃”的意义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开显。如果我们站在尼采的立场上来看克尔凯郭尔的“跳跃”,一个有趣的问题立刻就会出现——“跳跃”的落脚点在哪里呢?在克尔凯郭尔眼中,“跳跃”是“思想中的抒情性顶点”。“跳跃”不是米开朗基罗描绘的向天庭的飞升,“跳跃在本质上意味着,它是隶属于大地的,它要尊重重力定律,因此跳跃只是短暂的”。但在尼采眼中,“跳跃”是“背后世界论者”对人生此在的逃避。尼采说,那些创造神和彼世的人,皆因“痛苦和无能”,才“想一跃、致命一跃达到终极的疲倦,一种可怜的、无知的甚至不愿再意愿的疲惫”。尼采欣赏的意象是“攀登”,向往的是“漫游者和登山者”的生活,甚至是在高山上的生活,“跳跃”在他眼中是贬义的。尼采对“背后世界论者”及其“致命的一跃”的批判直指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这种批判当然是有道理的,只是它在克尔凯郭尔这里并不适用,因为克尔凯郭尔从来没有说过轻盈的“跳跃”的落脚点是“彼世”。相反,从写作《非此即彼》的时候,他就明确反对中世纪遁入修道院的举动,认为那是未能理解神爱的表现,是一种“小信”,因为从根本上说,神全知全能、自足圆满,神并不需要人的爱,爱神是出自人自己的需要。
到《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克尔凯郭尔提出“双重生存”的观点后,人的生存就被明确地置于有限与无限、时间与永恒的两极之间,经“跳跃”到“彼世”的意象进一步被消解。生存之所以艰难皆因两极间无法消解的张力,克尔凯郭尔称之为“生存的不适”,并且用形象的语言将之比喻为把一匹老马和一匹翼马套在同一辆车上行驶那样不匹配。倘若舍弃任何一极,生存都会轻松很多,比如舍弃有限的一极,像中世纪修道士那样只追求无限;或者舍弃无限的一极,像市侩那样在红尘中追名逐利。可以说,尼采对“背后世界论”的批判针对的是“双重生存”论确立之前充斥着迷信的宗教观,在这个问题上,一生为基督教随着社会世俗化进程而日渐式微操心的克尔凯郭尔比尼采“先进”。从生存论的角度出发,与单一维度的生存相比,“双重生存”的提出极大地拓展了生存样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出发,“双重生存”之下的信仰不仅是对路德“两个世界”观的推进,更符合经过了人神各司其职的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信仰观的需要。
德勒兹肯定是发现了克尔凯郭尔“跳跃”的妙处的。德勒兹持有“激进经验主义”的立场,或者说他相信存在着一个“经验主义的转向”,他认为相信此世,相信此世的生活,或者说在“内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上发现生存的方式是最困难的任务。在这个思想前提之下,德勒兹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中的“信仰的骑士”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信仰的骑士”完成了他的“跳跃”,在“跳跃”的瞬间他“跃出”了“内在性的平面”,成为超越者或信仰者。但这个“跳跃”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信仰的骑士”还通过“未婚妻和迷失的儿子”的形象“恢复”(restore)了“内在性”,留在了“内在性平面”之中,这中间他所需要的就是一点点“顺从”(resignation)。“未婚妻和迷失的儿子”的说法表明德勒兹熟悉克尔凯郭尔的生活故事,他对克尔凯郭尔有同情的理解,只是他没有止步于此,更没有被“信仰的骑士”及其所代表的与伦理决裂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从克尔凯郭尔的宗教思想当中德勒兹引出了自己的哲学运思:“跳跃”出“内在性平面”的行动只是暂时的,人最终仍然要落回到“内在性的平面”,而且要为“内在性”“充电”(recharge)。德勒兹发现了作为哲学家的克尔凯郭尔思想的当代价值,即克尔凯郭尔的核心关切不是上帝的超越性存在,而是信仰的维度所带来的生存方式和内在性的无限可能性。
齐泽克在《事件》这本小书中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的绝佳例证。齐泽克引用了克尔凯郭尔《重复》中假名作者以戏谑口吻说出的“一个头脑机智的人曾说过,我们可以把人类分成军官、侍女和扫烟囱的人”这句话,并郑重地称之为“克尔凯郭尔不朽的1843年对人的分类”。对于假名作者来说,这句话既“机智”又“深刻”,因为更好的分类需要更大的思辨才能。
如果按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假名作者口中“头脑机智的人”指的是丹麦黄金时代的美学和文化领袖海贝尔(J.L.Heiberg),还需要知道克尔凯郭尔与海贝尔充满戏剧性的关系。年轻的克尔凯郭尔自认是海贝尔派的美学家,他跻身于海贝尔和他的知名女演员夫人的文艺沙龙,并在那里赢得了机智优雅的名声。他后来因海贝尔对《非此即彼》的恶评改变了态度,视海贝尔为仇敌。即使如此,1845年,克尔凯郭尔为海贝尔的母亲、知名短篇小说作家托马西娜·居伦堡的小说《两个时代》撰写了《文学评论》;1848年,他在报纸上分四次发表了为早已隐退的海贝尔夫人撰写的《危机和一位女演员生活中的一次危机》。不难想象,齐泽克没有心思关心这些逸闻趣事,而且他看穿了克尔凯郭尔的反讽,认为克尔凯郭尔此言的“智慧”不在于如何对人进行分类,而在于“原则本身”,也就是那个多余的因素对于“二”的“增补”(supplement),齐泽克就“和谐的二”给出的例子是“阴—阳”。由此可以推论,齐泽克以独特的眼光引用的这句通常不为克尔凯郭尔研究者所重视的话,旨在表现“三”突破“二”的可能性,也就是多出来的“三”对原本平衡和谐的“二”的干预。
从列维纳斯对一元主义和总体性的警惕,到巴迪欧从爱始于两种“差异”的“相遇”而提出的“二”是“去中心化的立场”,再到齐泽克强调多余出来的“三”对和谐的“二”的突破,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哲学的结构和问题正在发生改变。对于齐泽克来说,他表达出的是“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和对生活的冲击力,其灵感居然来源于克尔凯郭尔《重复》中那么一句不起眼的话,这是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所带来的思想增益。
四、用还是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
在提出并分析了两种阅读克尔凯郭尔的方式之后,有人或许会问:究竟是应该用还是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来阅读克尔凯郭尔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克尔凯郭尔写作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他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克尔凯郭尔终生游离于体制之外,只是在受到《海盗船》攻击并感到自己继承的巨额遗产几近挥霍殆尽之际,才萌生结束作家生涯去当一名乡村牧师了此一生的念头,但最终也不了了之。特殊的生活境遇造就了他特殊的写作机缘,他一边靠遗产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一边勤奋写作,自费出书,并且为此而自豪,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像他的假名作者“爬天梯的约翰尼斯”在《哲学片断》中所说的那样,他的作品都是“亲笔所写,代表自己,一切后果自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拿自己的生活冒险,“郑重地与我自己的生活开玩笑”。至《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假名作者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要与时代背道而驰:当别人通过各种发明创造使生活变成容易的时候,他的目标是要使生活变得困难,具体言之就是打破他的丹麦同胞“生而为基督教徒”的习惯,让信仰重新成为充满激情的选择。
除了这项理想主义的高远任务外,作为一名不以写作为生的自由作家,克尔凯郭尔还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夹带私货”,通过写作与他终生无法释怀的未婚妻瑞吉娜进行“暗码通信”。克尔凯郭尔坦然地把《婚姻的审美有效性》和《反对婚姻的看法:一个丈夫的回应》这样的篇章分别收入《非此即彼》的下卷和《人生道路诸阶段》当中,他甚至还创作出《重复》这本小册子来“重复”他与瑞吉娜的婚约事件,只因他的写作“代表自己”。对这些“私货”的接纳和理解需要有对克尔凯郭尔生活境遇和写作的特殊性的了解,否则很容易陷入困惑和不解。
于是乎,在面对“用还是不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分两个不同的层次来回答:一个层次就是纯粹的阅读,像年轻的克尔凯郭尔以找到自己“能为之生、为之死的观念”为目标的阅读。那么,克尔凯郭尔不仅是一个恰当的阅读对象——如果读者能够接受他不拘一格的写作风格的话,而且用克尔凯郭尔的方式进入其作品还将成为一个必要条件,读者亦不必因为自己被克尔凯郭尔的文风所席卷而感到惭愧。另一个层次就是以研究者的态度面对克尔凯郭尔。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有必要了解克尔凯郭尔特殊的人生境遇和写作机缘,好的研究始于同情式的阅读和理解,也就是始于以克尔凯郭尔的方式阅读克尔凯郭尔,但研究者必须明确事情不能到此为止。好的研究者应该像侦探一样,能够透过克尔凯郭尔“间接沟通”的写作方式所制造的重重迷雾,直抵其思想的核心。更重要的是,面对克尔凯郭尔这样不按传统套路去思想和写作的人物,我们不能从既定的哲学和神学标准出发去阅读克尔凯郭尔;我们需要反其道而行之,从克尔凯郭尔的文本出发,去看他能为哲学和神学贡献出哪些新鲜的思想。
克尔凯郭尔以非学院派的写作风格突破了欧洲思辨哲学传统,使哲学开始面向鲜活的生活世界。这不仅是向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致敬,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哲学功能的重新界定。事实上,这个从作品出发而非从既定标准出发的思路不仅适用于克尔凯郭尔,它也是令哲学史资源当代化时必须遵循的原则。
五、结语:幸福的相遇是最好的阅读
最后让我们设想,倘若克尔凯郭尔穿越时空了解到了上述两种阅读其作品的方式,他会做何感想呢?克尔凯郭尔预见到了后世对他的人生和作品的兴趣,在1846年的一则日记中他曾经说,未来会有一天,当诗人讲述他完整的生活故事时,会让年轻姑娘兴奋得满脸通红。这句话背后隐含着克尔凯郭尔的自信和狡黠,他断定无人能完全参透他的人生和作品。如此,克尔凯郭尔应该会欢迎像德勒兹和齐泽克这样的哲学阅读方式,这种方式没有完全背离克尔凯郭尔的生活故事和写作风格,同时又把他的作品带入当代哲学的讨论之中,这是作者的幸福。
那么,用当代哲学的视角阅读克尔凯郭尔,会不会出现偏离克尔凯郭尔原意的可能性呢?举个例子,倘若克尔凯郭尔知道了阿多诺从社会批判角度对他的《爱的作为》所进行的猛烈抨击——克尔凯郭尔从作为“内心性”的爱的原则出发指出,重要的不是对穷人的救助,而是救助要以仁慈的方式进行,阿多诺批判这种仁慈是“无力的”甚至是“冷酷无情”的;克尔凯郭尔会接受阿多诺的批判吗?他会不会认为这个批判背离了他写作的原意呢?不,等等,克尔凯郭尔的原意?当克尔凯郭尔以他的“间接沟通”的方式打造出自己的作品天地的时候,他就已经亲手解构了自己的“原意”,而向着更多的阅读可能性敞开,余下的就要看作者与读者之间能否达成幸福的相遇了。显然阿多诺没有带给克尔凯郭尔作为一名作者的幸福感。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公众号2025年9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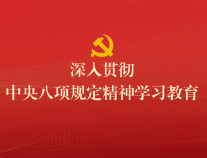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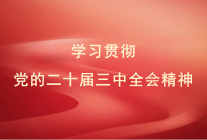



 潘梓年
潘梓年 金岳霖
金岳霖 贺麟
贺麟 杜任之
杜任之 容肇祖
容肇祖 沈有鼎
沈有鼎 巫白慧
巫白慧 杨一之
杨一之 徐崇温
徐崇温 陈筠泉
陈筠泉 姚介厚
姚介厚 李景源
李景源 赵汀阳
赵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