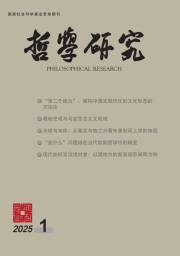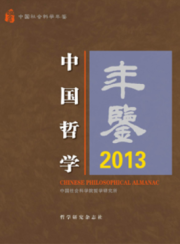【李震】宋代邵雍易学展开的三种趋向
内容摘要:北宋邵雍提出以《先天图》为核心的易学体系,受到宋代学者的重视,注释者代不乏人。两宋学者对于邵雍易学的诠释大体是在如下三种脉络中展开:郑夬、晁说之、朱震在汉易理路中解读邵雍易学的象数,强调其中的“错综变通之妙”;邵伯温、王湜、朱子更具宋易色彩,关注邵雍易学的义理内涵,发掘当中的“自然齐整之理”;术数派则将邵雍易学引向占算,以造成一种命定的历史观。汉、宋之别与学、术之别构成了邵雍易学在两宋和后世发展的基本线索。
关键词:邵雍 汉易 宋易 变通 定理
北宋邵雍以《先天图》为核心的易学体系,从根本处刷新了传统易学的诸多特质,可谓宋代象数易学之大宗与汉宋易学之转关。这种历史地位的取得并不只是邵雍个人之功,而应视为学派性的成果。由于诸多不同背景的学者的参与和诠释,自北宋而南宋,邵雍易学经历了一个学派逐渐建立、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1]考察这一复杂的诠释史,对于完整把握邵雍易学有重要意义。
宋代学者对于邵雍易学的诠释,大体是在汉易、宋易与术数三种走向中展开,当中尤以前两种为主。不同诠释脉络的对峙、交织,不仅组合成邵雍易学展开的基本线索,同时也体现出汉易向宋易整体的转换路径。
一、 邵雍易学的汉易诠释
邵雍易学具有一种可兼容或曰可沟通的复杂特质:不论是从事传统汉易的学者,还是具有更强的宋易自觉的学者,都在邵雍身上看到了各自关心的思想资源,都从自身理路出发对其作了有特色的诠释。汉易脉络下,北宋郑夬、晁说之与南宋朱震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与邵雍同时代的郑夬是较早深入发挥邵氏易学的学者。郑夬兼习刘牧与邵雍两派学术,[2]其留名后世则是由于“窃取”邵雍卦变说的历史公案。笔者曾论郑夬学说的特点在于从卦变而非成卦的角度阐发邵雍易学,此种卦变视角代表了当时学者的一般理解。[3]今推而论之,卦变其实是一种具有典型汉易风格的学说,汉易的乾坤二元论是其底色,故其说必以乾坤为诸卦之始,而非以太极为乾坤之本;关心的更多是如何描述变化的错杂过程,而非如何总结变化的确定原理。郑夬从卦变角度发挥邵雍易学,表明其人主要是在汉易的脉络下理解邵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梦溪笔谈》对郑夬卦变法的记录特别突出“乾坤错综”[4]四字,以见其特色与宗旨。这代表了汉易诠释的一个方向。
与郑夬从卦变角度呈现邵雍与汉易的关系不同,稍后的晁说之则主要是从卦气的角度将邵雍与汉易关联起来。晁说之出身中原文献世家,为学“博极群籍,尤长经术”[5],在易学上宗主孟、京、郑、虞的汉人之学,而痛斥王弼,以“使小王之说不得一日容也”[6]为职志。作为北宋屈指可数的汉易大家,晁说之却一生仰慕邵雍,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似乎表明邵雍学术在晁说之眼中与汉易具有某种亲缘性。事实正是如此。在晁说之看来,邵雍学说的殊胜之处在于其准确描述了变化的过程,特别能拟合自然节候的演变节奏,这正是汉易卦气说的目标。在《易玄星纪谱后序》中,晁说之谈到:
温公又本诸《太初历》而作《玄历》,其用意加勤矣,然简略难明。继而得康节先生《玄图》,布星辰,辨气候,分昼夜,而《易》《玄》相参,于中为极悉矣。(《嵩山文集》卷十,第3页下至第4页上)
晁说之认为,邵雍《太玄准易图》阐明了星辰、气候、昼夜的变化,才使司马光过于简略的《玄历》得以明晰。[7]这里,以卦爻、首赞拟配节候的邵雍易学,分明被视为一种卦气说。[8]邵雍将卦气说推展到了一个新高度,汉易至邵雍而更见光大,这是使得作为汉易学者的晁说之倾心服膺的原因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晁说之提出只有通晓京房易学者才“可以语邵康节之易”(《嵩山文集》卷十八,第6页上);而《传易堂记》的如下推重,也应在汉易的意义上得到理解:
惟康节先生,天资既卓越不群,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学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错综变通之妙始大著明矣。(《嵩山文集》卷十六,第11页上)
由晁说之学术的宗旨观之,这里的“错综变通”大概不是指郑夬式的卦变说,主要应指卦气说而言。不过,作为一种宏观定位,“错综变通之妙”六字不妨说是涵盖了卦变与卦气两个方面,从而概括出了邵雍易学在汉易学者眼中的整体特色:邵雍之学的成就正在于细腻地刻画出了变化的复杂性。这种理解,与后来朱子等人在邵雍身上读出的“自然齐整之理”有深刻的差异。
南渡后扬名的朱震是宋代汉易象数学的另一重镇,其对邵雍易学的诠释与上述两位又有区别,主要是在图象的角度下展开的。在著名的《进周易表》中,朱震对北宋五子及刘牧的易学有如下判摄:
故雍著《皇极经世》之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述《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等篇。或明其象,或论其数,或传其辞,或兼而明之,更相唱和,相为表里。(《通志堂经解》第1册,第194页)
从朱震在《汉上易传》正文中特重横渠之学的态度来看,他这里的“兼而明之”是指张载而言,即认为只有张载易学做到了象、数、辞的兼顾;而邵雍、程颐等各家则“或论其数,或传其辞”,不免各有局限。理解这一点对于把握朱震的相关论述十分重要:或许是由于对邵雍以数为本的易学理解和评价有限,《汉上易传》很少从数的内在理路诠解邵雍;相反,其论述往往是从象与图等其他视角作出的,表现出整合、改造的意味。
朱震在对《说卦传》的解释中,较集中地征引了邵雍易说,如:
1. 引邵雍“月为寒”“水遇寒则结,遇火则竭,从所胜也”之语,以说明“乾为寒,为冰”;
2. 引邵雍“天依形,地附气,其形有涯,其气无涯”之语,以说明“坤为地”;
3. 引邵雍“君子以万物为舆马”“群者,通阴阳言之”之语,以说明“坤为大舆”“为众”;
4. 引邵雍“枝干,土石也,故岁不易;叶花,水火也,故岁易”之语,以说明“(离)其于木也,为科上槁”;等等。(《通志堂经解》第1册,第263-264、268页)
《汉上易传》引用邵雍的条目不多,此类解释约占其间的一半。这些解释有一个特点:其所引文字本是邵雍观物之学的内容,却被朱震用作说明八卦取象的根据,这实际上就是要将邵雍的观物学转变为汉易的取象说。学者指出,南宋初年有一汉代象学的复兴潮流,朱震是当中最重要的代表。[9]《汉上易传》通篇最重要的解释手法就是取象。朱震的上述解释,牵引邵雍本意以从己说,正体现出从象学角度将邵雍纳入汉易的努力。
除取象外,朱震以汉易统摄邵雍的另一手段是借助易图。《周易卦图》录有多种与邵雍易学有关的图式,其中不太引人瞩目的一种是所谓《纳甲图》。(《通志堂经解》第1册,第283页)实则此图颇有深意。朱震记录的《纳甲图》,在卦位顺序上遵从的是虞翻及《周易参同契》的月体纳甲说,但在卦图形式上却刻意采取了与邵雍《伏羲八卦圆图》(通常称《小圆图》)相同的做法,即将八卦按《小圆图》的形式排列成圆。这种设计不是偶然,而是要在《小圆图》与《参同契》等的纳甲学说间人为勾连起关系。纳甲在汉易中不是一种孤立的方法;经由纳甲,包括五行、八宫、爻辰在内的种种汉易手法都能得到运用。朱震所载《纳甲图》的真正意义,似是在使邵雍易学经由纳甲而与汉易之整体获得沟通的途径,从而也就是将邵雍易学更彻底地整合到汉易当中去,尽管这种尝试只是初露端倪,尚未完全展开。[10]
从郑夬到朱震,宋代的汉易论述留意到邵雍的思想资源,并努力在卦变、卦气、取象、易图等视角下加以统摄,其意在于使邵雍易学更彻底地融入汉易,以便更好描述变化的过程。这种统摄自有其根据:作为一种“数学”,邵雍易学以借助数字准确刻画阴阳消长为追求,这与汉易的精神深有契合;卦变、卦气等议题因而也就是邵雍易学的重要内容。但这种统摄终究未能较彻底地完成,除去学术思潮进退的偶然因素外,更根本的原因乃在于,邵雍易学自有其不能被完全化归为汉易的复杂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汉易学者的上述诠释普遍较少用到邵雍易学的核心材料,诸如六十四卦之成卦、《先天图》之方位与象数,以及太极、两仪、四象关系等关键问题,基本是在上述汉易诠释的范围之外。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需要一种与汉易不同的解读方式。[11]
二、 邵雍易学的宋易诠释
不同于朱震等人,北宋邵伯温、南宋王湜与朱子等学者在解读邵雍易学时,基本不引入汉易的体例和手法,而是阐发邵雍易学的义理问题;即使是在解释邵雍易学的象数论题时,关心的也更多是核心象数模式中的义理意蕴。其说具有典型的宋学风格。
邵伯温作为邵雍嫡子,毕生致力于光大乃父的影响,撰写了多篇推尊邵雍的文字。其在邵雍学术上之较为实质性的贡献,是注释了《观物内篇》。在邵伯温的注释中,对太极与天地之心的解释特别能见出宋易的特色:
夫太极者,在天地之先而不为先,在天地之后而不为后,终天地而未尝终,始天地而未尝始,与天地万物圆融和会而未尝有先后始终者也。有太极,则两仪、四象、八卦,以至于天地万物,固已备矣。非谓今日有太极,而明日方有两仪,后日乃有四象、八卦也。虽谓之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实一时具足,如有形则有影,有一则有二、有三,以至于无穷,皆然。[12]
这段文字中,太极被认为具有某种本体的非时间性,且两仪、四象、八卦的生成过程也是“一时具足”,无先后次第可言。邵伯温的这种解释,与后来朱子关于成卦过程“有则具有”[13]的主张十分相似,而与秦汉思想中被理解为宇宙之早期阶段的太极明显不同,有更强的本体色彩。
邵伯温太极解释的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将太极与理学话语明确结合起来:
万物无所不禀,则谓之曰命;万物无所不本,则谓之曰性;万物无所不主,则谓之曰天;万物无所不生,则谓之曰心。其实一也。古之圣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0册,第214-215页)
二程曾言易、道、神等皆天之一义,而帝、鬼神、乾等等也不过是对天“分而言之”的称呼。[14]邵伯温在邵雍身后问学于程门,其将命、性、天、心统一于太极的思路和言说方式,明显带有二程的痕迹。邵伯温又引《说卦》《孟子》,将邵雍的太极学说导引到理学核心的理性命、心性天结构中来,用意同样在于使邵雍与二程理学相接合,以为邵学发展打开途径。
不过,在借助二程阐释邵雍的同时,邵伯温也注意为两者划开距离,这在其对天地之心的讨论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世儒昧于易本,不见天地之心。见其一阳初复,遂以动为天地之心,乃谓天地以生物为心。噫,天地之心何止于动而生物哉!见其五阴在上,遂以静为天地之心,乃谓动复则静,行复则止。噫,天地之心何止于静而止哉!为虚无之论者,则曰天地以无心为心。噫,天地之心一归于无,则造化息矣!盖天地之心,不可以有无言,而未尝有无,亦未尝离乎有无者也;不可以动静言,而未尝动静,亦未尝离乎动静者也。故于动静之间有以见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0册,第231页)
邵伯温认为邵雍的“一动一静之间”最能贴合天地之心,而动、静、无都是对天地之心性质的误解。其中,以动为心即程颐之说。(《二程集》,第819页)以邵伯温对二程学说的熟悉,他这里的评论明显有针锋相对的争辩意味。伯温之子邵博曾提到南宋初年程门后学与邵学之间既相亲近,又有紧张;[15]邵伯温对二程理学既借重又批判的态度,反映出其在处理程邵学术关系时的微妙考虑。
与朱震大体同时的王湜,在学术史上声名不显,但对邵雍易学却有到位的诠解,是张行成、朱子以前最系统的邵学学者。王湜《易学》在以邵解邵的前提下,较多启用了分析思辨的方式,其说清通简要,颇能挖掘出邵雍易学的义理内涵。如其论四象云:
阳中有阴,阴抱阳而下降,阴降而阳亦降矣,所以能交于地也。……阴中有阳,阳负阴以上升,阳升而阴亦升矣,所以能交于天也。(《通志堂经解》第1册,第99页)
邵雍易学中有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观物外篇》言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但阳性趋上,何以能下交?阴性趋下,何以能上交?《观物外篇》的说法似与阴阳性质相悖。后来朱子及其后学引及此句时,多将上下二字颠倒,以避免解释上的困难。[16]王湜则给出了一种颇具哲学性的解释:邵雍说法的根据正在于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每一存在的内部都涵蕴着对立性的力量,一种力量与其对立面相抱合、牵引而造成变化,这就是阴阳之运动所以能与自身本性相反的原因。王湜将阴阳互涵这一邵雍已有的观念推广到对生成运动问题的解说,其论述风格不仅是义理化的,而且构成对于邵雍易学的推进。
以类似的分析思辨的方式,王湜讨论了八卦体用、先天后天方位等邵雍易学的核心问题。当中的细节不必详言,但王湜的解释颇以理观念为根据,此种形式性的特征值得留意。如论八卦卦象之变与不变,则言:“阴阳之理,交则变,不交则不变。”论《河图》《洛书》、九数十数之关系,则言:“然则天地数增九以为十,卦数减九以为八,岂圣人之私智哉?皆自然之理而已。”(《通志堂经解》第1册,第100、102页)在王湜稍后的张行成笔下,“自然之理”“理之自然”这样的说法作为解释性的根据更是大量出现。邵雍虽以观物之理闻名,但其论述中其实甚少使用“理”概念作为解释性的根据,更罕曾言及“自然之理”,“理”在邵雍哲学中的主要作用只是凸显存在的确定性;真正使“自然之理”获得对现象之解释效能的,是二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过邵伯温时代的导引,及至王湜、张行成,二程理学已经有深度地介入了邵雍易学,成为解释邵雍的重要方法。[17]
南宋邵雍诠释中影响最大者无疑是朱子。通过讲明成卦方法,朱子廓清了此前邵雍易学中长期存在的成卦与卦变主题之争;通过引入先天横图,朱子为邵雍易图的诠释提供了新的面向。除去这些“实”的内容外,朱子对邵雍的诠释中尚有不甚为人注意的“虚”的方面,即其特定的诠释角度:朱子是有意用“理”来理解邵雍。在根本概念上,朱子认太极为理的观念提供了邵雍易学与程朱理学接榫的途径;[18]在学问性质上,朱子认为邵雍的数学其实就是理学。《朱子语类》载:
康节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转,久之理透,想得一举眼便成四片。……盖理在数内,数又在理内。康节是他见得一个盛衰消长之理,故能知之。
或问康节数学。曰:“且未须理会数,自是有此理。……盖其学本于明理,故明道谓其‘观天地之运化,然后颓乎其顺,浩然其归’。若曰渠能知未来事,则与世间占覆之术何异?其去道远矣!其知康节者末矣!盖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见,便不待思量。”(《朱子语类》卷一百,第2546页)
邵雍之学以数闻名,但在朱子看来,数本于理,理数一体两面,邵雍对数的探讨只是其明理的表现。这就从根本上将邵雍易学的主题收束到了理的范围之内。朱子又特别强调邵雍所言易理之“自然齐整”的特点:
然圣人当初亦不恁地思量……自一为二,二为四,四为八,八为十六,十六为三十二,三十二为六十四。既成个物事,便自然如此齐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圣人手画出来。
问:“先生说:‘伏羲画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虑,只是借伏羲手画出尔。’唯其出于自然,故以之占筮则灵验否?”曰:“然。自‘太极生两仪’,只管画去,到得后来,更画不迭。正如磨面相似,四下都恁地自然撒出来。”(《朱子语类》卷六十五,第1605、1612页)
“自然”指的是无心无为,不假安排;“齐整”指的是一阴一阳,条理粲然。这是说,六十四卦的成卦原理极其简单,只是“一阴一阳”这一简单原则的不断应用,并无刻意造作的成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晁说之等汉易学者,朱子对邵雍易学之特质的理解已从“错综变通之妙”转向了“自然齐整之理”。在朱子看来,邵雍易学的高明之处不是在于细致追摹了变化的过程,而是在于提炼䌷绎了变化的原理;定理的确定性、秩序感而非变通的曲折性、复杂度才是朱子及其时代的思想精神。这里的“自然齐整之理”,当然也是接续着前文所论程颐以来“自然之理”“理之自然”的思想脉络发展而来的。
从邵伯温、王湜到朱子,以理观念为根据,邵雍易学的结构被勾勒得越来越清晰、简明,理对于邵雍易学的整合与奠基越来越深入;与此同时,此前汉易学者关注的邵雍易学的许多重要内涵,在这一理则化的过程中则被抛弃、简化或者省略掉了。作为所有这些过程之结果的是,一种邵雍易学的新面貌由此正式登场,而一种宋学精神的新周易观也自此基本定型。
三、 术数诠释与汉宋流变
汉易与宋易之外,邵雍易学在宋代的展开还有另一重趋向,即其与术数的纠葛。此非哲学史研究所欲详论,大体而言,邵雍易学在宋代的术数化是沿两条脉络展开:一脉是“自云传邵雍之学于司马温公”(《郡斋读书志校证》,第46页)的北宋牛师德、牛无邪父子,以所谓司马光秘传的邵雍《太极图》与衍卦法为依傍,铺演成一套复杂的卦气系统,其说得张行成保存,后来传者不绝;另一脉是较早见于南北宋之交、亦为朱子称引、而被《梅花易数》等托名占书发扬光大的数字占法,此脉在后世更为知名。两说同属术数命定论,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一套系统的援易入历、以卦配时的方法,将历史的每一步骤都视为预定;后者则是在悬置历史整体之可知与否的前提下,窥探未来某一特定时点的吉凶。若就本文所论汉宋学术的区别言之,大要可说,前一脉以卦气说为方法,其错综变通的进路较近于汉易;而后一脉对描摹变化之整体性全不措意的态度,则表现出某种走出汉易的意味。汉宋的差异在发挥邵雍易学的术者群体中也有曲折的表现。
三种趋向中,术数趋向既不是邵雍易学自身的精神,也难成其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易学形态,真正有学理意义的主要是汉宋两家。依常理而言,汉易与宋易对邵雍易学的理解既有重大不同,原本应有直接的交锋;交锋之后,新的主导性的易学形态方能建立。然而宋代易学史的发展特点是,以朱震为主要代表的汉易路向仅仅在南宋初年短暂复兴之后寻即偃息,并未形成持续的力量,更没有与以朱子为代表的宋易路向发生直接的争论。当朱子登上易学史的舞台时,朱震的声势早已消歇。于是,这场本该发生的对峙最终是以一方的提前退场告终,朱子通过以成卦取代卦变式的解读“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宋代易学中的汉宋之争。此后,在宋明时代,邵雍易学其实已经被整合进入朱子学中,成为了朱子学体系的一个部分;而其被朱子摆落或未进入朱子视野的内容,则少有问津,湮没在了历史的角落中。
不过,这场“悄无声息”的胜利并不彻底。由于汉宋争论未曾展开、学理互动不够深入,汉易在朱子时代并未真正被驳倒,更多只是被省略与隐藏;待到明清之际,便重新开始成为流行的易学风潮。这种风潮表现在邵雍易学的接受上,就是朱子及其先行者所建构的以“理”为主导的邵雍易学的面貌不再为人所关注;反过来,在黄宗羲、胡渭等人笔下,卦变、卦气、方圆等汉易视角在结合了宋易图书之学等内容后,重新成为理解邵雍的重要途径。邵雍易学的形象与内涵因此一直在汉宋之间保持着某种张力。另一方面,如同汉、宋之争未有定局一样,邵雍身上的学(学理)、术(术数)之争也并未随着朱子的综合便消失。在朱子学占据胜场的精英与官方学术外,南宋至元代,四川、江右等地始终有学者、术士致力于阐发邵雍思想极数知来的功能,如祝泌、廖应淮等,通过将卦爻进一步与历史、声音相配比而起卦占验,构成牛无邪、张行成之学的余波。此种学问风格颇能代表一般士人和百姓对邵雍的理解,且反过来影响到精英士人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学、术之争也一直延贯于邵雍易学展开的始终。本文希望讲明的是,塑造上述学风进退与面貌虚实的更深沉的学理上的力量,始终是在“错综变通之妙”与“自然齐整之理”之间。
【注释】
[1] 本文讨论的邵雍易学学派的主体,并不是师承意义上的邵雍亲传弟子,而是思想意义上的对于邵雍易学作出了代表性诠释的后世学者。从历史上看,王豫、张崏等邵雍弟子或无名、或早逝,多不能显扬师说;真正使邵雍具有重大影响的,是朱震、朱子这样的后世诠释者。
[2] 晁公武引姚嗣宗之说,以郑夬为刘牧二传弟子(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4页);邵伯温认为郑夬是因求学邵雍不得而窃取其遗说(邵伯温:《易学辨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8页),则郑夬又为邵氏门人。这两种说法未必矛盾,盖刘牧之学传于南方,邵雍之学盛于洛阳,郑夬以南人而游于河南,可能确曾与闻两家之学。
[3] 关于郑夬卦变说的背景和方法,参见拙文:《从邵雍到朱子:“一分为二”说的演变与定型》,载《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6期。
[4] 胡道静:《梦溪笔谈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9页。
[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1334页。
[6] 晁说之:《太极传后序》,《嵩山文集》卷十七,《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7页下。
[7] 晁说之既追随司马光学易,又深服膺邵雍易学;既重司马光《玄历》,又取邵雍《玄图》“合而谱之”(《易玄星纪谱后序》),他对于两家易学的推崇不是偶然、孤立的,也不只是因为邵、马二人交谊深厚遂爱屋及乌,而是有更深的理论上的原因:从汉易来看,邵雍与司马光都是卦气说的继承者,其学理形态有内在的相近处。
[8] 此种卦气说的内涵,从传世的《太玄准易图》可以有直观的认识。(参见朱震:《周易卦图》卷中,《通志堂经解》第1册,江苏广陵古籍刊印社,1996年,第278页)
[9] 王铁:《宋代易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
[10] 在易图与取象之外,朱震还接续郑夬的说法,从易学史观上统摄、整合邵雍易学。朱震在《周易卦图》中评述说,郑夬自称从《归藏·初经》中得到了邵雍的《伏羲八卦图》,而伏羲之易两两相对的八卦方位也正相当于《归藏·初经》的八卦次序,因此邵雍的伏羲之易就相当于传统三易说中的《归藏》。(《通志堂经解》第1册,第273-274页)三易说较早见于汉代王充、郑玄等人的论述,郑夬、朱震将邵雍与《归藏》关联起来,虽未必是历史的真实,却使得邵雍易学开始被较深地整合到传统的易学史观当中去。此后,南宋不少学者接续朱震之说,三易说日渐丰富;而邵雍与三易说的关系,亦在张行成等人的发挥下愈见复杂。
[11] 南宋张行成的邵雍解释中也有汉易成分,如其《易通变》对卦变所作的接近郑夬的解读,以《既济图》为代表的若干图式中的卦气说,等等。但应指出的是,张行成身上的汉易属性远不能与上述三位并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张氏之学庞大芜杂,宋易、术数之说都有网罗,难以一端言之;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张行成基本是沿邵雍易学的思路规模展开发挥,而不是站在汉易立场上统摄邵雍易学。因此,本文不将张行成简单划入三种趋向中的某一类,而将其视为邵雍易学之较为“本位”“集成”但又“主观”的诠释者。
[12] 胡广编:《性理大全》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0册,第214页。
[1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第1667页。
[14]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周易程氏传》卷一,《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4、695页。
[15]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第45-46页。
[16] 谷继明与陈睿超都提到了这一点。(胡方平、胡一桂:《易学启蒙通释·周易本义启蒙翼传》,谷继明点校,中华书局,2019年,第87页;陈睿超:《朱子易学对〈先天图〉与〈太极图〉的交互诠释》,《周易研究》,2021年第1期)
[17] 王湜不仅用理概念诠解邵雍,还将《河图》《洛书》及周敦颐的哲学与邵雍相结合;张行成的解释则较多引用张载之说。这些都体现出南宋邵学的综合趋势。
[18] 朱子认为,邵雍成卦说中的“太极生两仪”就是“一理之判”。(朱熹:《答虞士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57页)
原载《中国哲学史》,2025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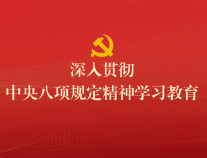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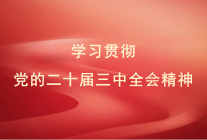



 潘梓年
潘梓年 金岳霖
金岳霖 贺麟
贺麟 杜任之
杜任之 容肇祖
容肇祖 沈有鼎
沈有鼎 巫白慧
巫白慧 杨一之
杨一之 徐崇温
徐崇温 陈筠泉
陈筠泉 姚介厚
姚介厚 李景源
李景源 赵汀阳
赵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