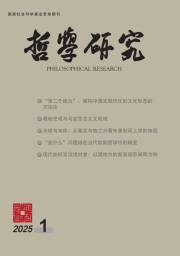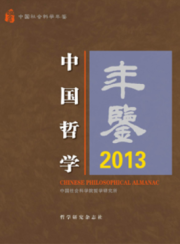【龙涌霖】言说方式、经典解释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言说方式”(又称“论说方式”)的提法受启发于陈少明老师《“四书”系统的论说结构》[1]一文。它是指文本思想内涵之外的表达形态、说话风格、文学体裁等,亦即内容之外的形式性的东西。例如《大学》的言说方式是纲领式的,《中庸》最具特色的言说方式则是神秘性玄言,而在《论语》则体现为师生之间的日常对话。当若干言说方式各异的文本组合、熔铸成一个思想体系时,我们就称其言说方式为“言说系统”或“论说结构”,典型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注经体系。对言说方式、论说结构的关注是陈老师论述整个经典文化中的重要一环。经典并非只提供概念和命题。要整全地理解经典,还需充分考虑到经典展现的广阔而活泼的生活世界、经典文本的传播和意义再生、经典与历史的互动,以及经典的思想史背景等等方面。正如陈老师常用的一个生动譬喻,他要看到的是整个经典森林体系的“土壤、气候、阳光、水分”等等要素。[2]而言说方式作为经典显示自身的形态,自然也会进入陈老师的视野。在《“四书”系统的论说结构》一文中,我们看到儒学从孔门中的原初伦理形态,一路发展到朱熹通过注经而塑造的一套贯通天人的思想体系,其言说方式不断在丰富和融合,由此使我们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到深层的思想文化经验。陈老师的这一考察工作有他一贯的关怀,即对儒学趋于学理化、抽象化,从而脱离日常生活的反思。他抛出的问题是,在共享特定信仰的传统学术共同体瓦解、注经方式难再奏效的当下,我们如何继承四书学乃至传统文化这一伟大的遗产,让中国哲学仍具说理力量?
笔者不揣谫陋,想结合《大学》诠释史的问题指出,言说方式这一视角对于深入考察经典解释的发展机制,乃至思考如何在古代经典的基盘上“做中国哲学”,都具有十分有前景的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大学》是理学工夫论的核心文本,宋明儒者格物穷理、诚意慎独等工夫主张都需要在此篇找到经典依据。但我们参考陈来老师的研究,会看到汉唐儒者对此篇主旨的把握更多是外在的为政论而非内在修行的工夫论,亦即其重心在“修齐治平”,而非“格致诚正”。[3]事实上汉唐儒者的理解更接近《大学》作者的意图,因为《大学》对修齐治平四目的逻辑建构是很完备的,如“齐其家在修其身”“治国必先齐其家”“平天下在治其国”的表述,而对于格致诚正四目只给出“修身在正其心”一环,其逻辑紧密相对欠缺。而且“格物致知”章并没有像程朱说的那样脱简了,据梁涛老师的研究,它实际上讲的是对首章“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认知。[4]这很可能就是《中庸》讲的“凡事豫则立”及“道前定则不穷”,实即指追求“天下有道”的士君子在行动前对于行动步骤有清晰的认知和规划,亦即弄清修齐治平孰先孰后的问题,这里面并没有很浓的理学工夫论味道。
因此,当二程和朱熹要重新解释《礼记》中这一文本的时候,就不仅是在思想内涵层面引入理学概念作解释那么简单。注经作为一种言说系统建构,实际上包含着极复杂的在文本言说方式层面的剪辑、拼接、改造、配套、转移等一系列重塑工作。简单说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判定文本脱简。这一步是二程兄弟的工作。应当说,脱简之说在当时的认知能力和条件下是比较合理的解释,由此打开了“格物致知”的诠释空间,为后来朱熹顺理成章地作理学式《补传》创造了条件。第二是分经分传。朱熹将《大学》首章判定为孔子所作,极大提高了《大学》的地位,使其具有工夫论经典依据的资格。第三是为《大学》作长序。朱熹的这一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以往郑玄、孔颖达对《大学》所作的题解都非常简略,而朱序则为《大学》提供了一套立足于三代政教、尽心复性的伟大叙事,以及一条孔、曾、孟的道统谱系,这也一下子拔高了《大学》的地位,为理学式解释埋下伏笔。第四是解释重心的悄然转移。以往我们考察经典解释的时候,倾向于关注注家用什么新概念来解释文本,却较少去琢磨注家在文本的哪些章节段落上他们为什么不提出新解释,而是选择“留白”。这其实也是注经这一言说方式的非常关键的一步。朱熹对格致诚正提出了很多崭新的理学解释,对修齐治平则淡化了很多,更多在沿用旧注。尤其我们注意到,在《大学章句集注》末尾,朱熹还叮嘱学者尤当留心用功于“格物致知”和“诚意”两章,这恰恰是他自己理学化解释味道最浓的地方。通过这种言说系统的重新塑造,朱熹就淡化了原本《大学》对修齐治平的强调,不知不觉间把重心转向了格致诚正的内在工夫,从而为理学的新解释奠基。
可见,经典解释的发展并非只是把经典文本作为空瓶子来注入新概念那么简单。注经背后往往是一系列复杂的言说方式、话语体系的重新塑造,言说方式的更新使经典的新生得以可能,这需要我们能立体地把握这一动态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言说方式对于更深入把握经典解释学的发展机制,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视角,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回到陈老师提出的问题,如何让当今中国哲学更具说服力呢?在笔者看来,除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和论域上需要推陈出新,在言说方式的层面也需要有自觉意识。实际上陈老师“做中国哲学”的工作本身正是一种言说方式转化上的典范。在儒家经书不再具有政治权威的后经学时代,单纯注经的方式显然无法满足传统哲学面向未来进行说理的需求,通过现代汉语表述的现代学术论文大概更能符合哲学表达的时代需要。陈老师以其通达、凝练、流畅、隽永的文章风格已在学界独树一帜。但更为关键的是,陈老师有意淡化西方哲学传统下围绕概念、命题、体系的枯燥写作,以及冯友兰先生传统以来对中国哲学经典中原有的形而上学概念体系的注重。他更喜欢直面“经典世界”中活生生的人、事、物,《论语》中的师徒日常对话,《庄子》中神乎其技的庖丁、乐乎濠梁的鱼儿以及庄子、惠施的斗嘴,乃至宋明理学中格竹、观花等公案,都栩栩如生,富含哲理。从具体的古典生活经验中讲出通达古今的普遍事理,陈老师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展现了一幅富有生命力的前景。这也是一种言说方式的悄然转化。由此笔者觉得,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或许也可以走出一条“新瓶(言说方式)装新酒(思想内涵)”的道路,但保留并提纯了传统的味道和神韵,即既在思想内容上日新日成,相应地也需要发展出符合时代的新的说理方式,从而把中国哲学做得更有说服力。
【注释】
[1] 见陈少明《仁义之间:陈少明学术论集》,贵阳:孔学堂书局有限公司,2017年,第44-74页。
[2] 见陈少明《什么是“经典世界”?》,《中国哲学年鉴》2017年。
[3] 见陈来:《〈大学〉的作者、文本争论与思想诠释》,《东岳论丛》2020年第9期。
[4] 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6-128页。
原载:陈少明等著,程乐松、张任之、陈壁生编:《思想的手法:如何“做中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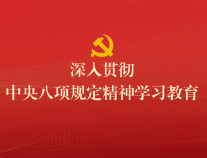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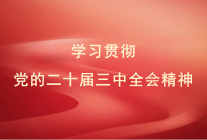



 潘梓年
潘梓年 金岳霖
金岳霖 贺麟
贺麟 杜任之
杜任之 容肇祖
容肇祖 沈有鼎
沈有鼎 巫白慧
巫白慧 杨一之
杨一之 徐崇温
徐崇温 陈筠泉
陈筠泉 姚介厚
姚介厚 李景源
李景源 赵汀阳
赵汀阳